人类语言能力的自然演化:乔姆斯基对阵达尔文|《达尔文的危险思想》

导语
查尔斯·达尔文用他的《物种起源》为生命的多姿多彩提供了一种解释:是演化和自然选择造就了这个星球上缤纷的生命。然而自诞生的那一天起,达尔文自然选择和演化的理论就引发过很多争议。很多人认为,人类语言能力的演化不能用达尔文式的自然选择来解释。诺姆·乔姆斯基,世界上最伟大的语言学家,以及斯蒂芬·杰·古尔德,世界上最著名的演化理论家,就曾一再表示语言可能不是自然选择的产物。
在《达尔文的危险思想》中,丹尼特基于科学事实和缜密的逻辑论证提出,演化是一个机械的算法过程,这种算法过程不仅决定了羚羊的速度、老鹰的翅膀和兰花的形状,也同样决定了心灵、意义、道德等概念。丹尼特把对演化和自然选择的论述从生物学领域拓展到了文化、语言、社会等生物学以外的其他领域,把对演化和自然选择的理解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本文节选自《达尔文的危险思想》第十三章。
研究领域:语言演化,自然语言,人工智能,认知心理学,自然选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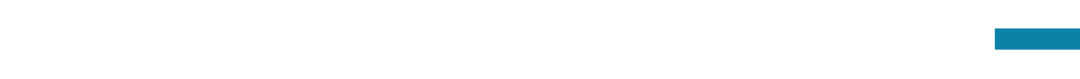
[美] 丹尼尔·丹尼特 | 作者
人们可能会认为,乔姆斯基只要把他那颇具争议的、关于语言器官的理论建立在演化论的稳固基础之上,那就万事大吉了,况且他在自己的一些著作中也暗示过某种这样的联系。但他在更多的时候对此持怀疑态度。 ——斯蒂芬·平克(Pinker,1994,p.355)
至于语言或翅膀这样的系统,我们甚至很难想象出可能让它们得以产生的选择过程。
——诺姆·乔姆斯基(Chomsky,1988,p.167)
一边是一批认知科学家,他们有的通过人工智能进入该领域,有的则是通过研究解决问题的行为和形成概念的行为,另一边是通过关注语言问题进入该领域的人,双方仍然存在着相当大的隔阂……当语言过程作为一种人类能力的独特性得到强调的时候—乔姆斯基就是这么做的……,这种隔阂就会加剧。
——赫伯特·西蒙与克雷格·卡普兰 (Simon and Kaplan,1989,p.5)
1956年9月11日,无线电工程师学会(Institute for Radio Engineers)在麻省理工学院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宣读了三篇论文。
其中一篇是艾伦·纽厄尔和赫伯特·西蒙的《逻辑理论机》(NewellandSimon,1956)。二人在文中首次展示了一台计算机如何能够证明重要的逻辑定理。他们谈到的这台“机器”是他们后来的“通用问题解决器”(GeneralProblem Solver)(Newell and Simon,1963)的父亲(或祖父),也是计算机语言Lisp(表处理语言)的原型,而Lisp对于人工智能的意义大致就像DNA代码对于遗传学的意义。若要角逐“人工智能界亚当”的美名,逻辑理论机足以同阿尔特·塞缪尔的跳棋程序匹敌。
第二篇论文是心理学家乔治·A.米勒的《一个神奇的数字:7±2》,这篇论文后来成为开创了认知心理学领域的经典论文之一(Miller, 1956)。
第三篇论文的作者是一名27岁的哈佛大学初级研究员,名叫诺姆·乔姆斯基,论文的题目是《语言描写的三种模型》(Chomsky, 1956)。任何回溯性加冕都难免会有些武断,这已经屡见不鲜,但乔姆斯基在无线电工程师学会的演讲作为现代语言的标志性事件,绝对是名副其实。
三大新兴科学学科在同一天诞生于同一个房间里——不知道当时的听众中有多少人感觉到自己正在亲身经历一个如此有分量的历史事件。乔治·米勒就感觉到了,他后来对那次会议的描述(Miller,1979)向我们表明了这一点。而赫伯特·西蒙在回顾这场会议的时候,其观点则随时间的推移而变化。在1969年出版的书中,他提请人们注意这个非比寻常的时刻,并说道(Simon,1969,p.47):“因而这两块理论[语言学和人工智能]在早期就有着亲切友好的关系。千真万确,因为它们都以同一种人类心灵观作为自己的观念基础。”真要是这样就好了!等到1989年,他就能看到双方的隔阂已经扩大到了怎样的地步。
在众多的科学家中,伟大的科学家少之又少,而在伟大的科学家中,能够发现一个全新领域的人更是少之又少,但毕竟还是有几个。查尔斯·达尔文是一个,诺姆·乔姆斯基又是一个。在达尔文之前就有生物学——博物学、生理学、分类学等等——这些都被达尔文统合成了我们今天所知道的生物学。无独有偶,在乔姆斯基之前就有语言学。作为当代科学领域的语言学,有语音学、句法学、语义学和语用学等子学科,有交战不休的学派和自立门户的分支(比如人工智能中的计算语言学),还有心理语言学和神经语言学这样的子学科。语言学从各种不同的学术传统中成长而来,可以追溯到一系列先驱的语言探究者和语言理论家,从格林兄弟到费尔迪南·德·索绪尔和罗曼·雅各布森,可这一切都在一位先驱者——诺姆·乔姆斯基——率先实现的理论进展下,被统合成了一个富含内部联系的科学探究家族。
在1957年出版的小书《句法结构》中,他把自己之前一项雄心勃勃的理论探究的成果应用到了自然语言(如英语)上,这项理论探究是在设计空间中的另一个片区进行的:该片区是个逻辑空间,其中是能够生成和辨认所有可能语言之语句的所有可能算法。乔姆斯基的工作严格遵循图灵的探究路径,图灵的纯逻辑探究关注的是我们现在称作计算机的这种东西所具有的力量。乔姆斯基最终界定了一个关于语法类型或语言类型的阶序——乔姆斯基层级(Chomsky Hierarchy),所有学计算理论的学生至今仍能靠它初窥门径。他进而展示了这些语法如何能够同另一个阶序相互界定,后者由各种自动机或计算机类型构成——从“有限状态机”,到“下推自动机”和“线性有界机”,再到“图灵机”。
几年后,当乔姆斯基的研究第一次进入我们的视线时,它在哲学界掀起的冲击波令我记忆犹新。那是1960年,我在哈佛大学读大二,当时我问奎因教授,在那些批评他观点的人中,有谁的作品是我应该读的。(当时我自认为是冷酷无情、信念坚定的反奎因派,并且已经开始在为我的毕业论文拟定论点,而这论文当然是要攻击奎因的。所以凡是在观点上反对奎因的人,我都必须了解!)他当即建议我去读读诺姆·乔姆斯基的研究。当时哲学界很少有人听说过这位作者,但他的名气很快就盖过了我们所有人。
语言哲学家们对他的研究反应不一。有些人爱,有些人恨。我们中间爱他研究的人,很快就清一色地搞起了转换、树状图、深层结构以及其他各类可以算作某种新形式主义的神秘玩意儿。在恨他研究的人中,有许多人谴责这是一种庸俗的科学主义,是一群带着科技范儿的焚琴煮鹤之徒在丁零咣啷地发起攻击,妄图破坏语言那优美动人、无法分析、无法形式化的精妙之处。在几所主要大学的外语系中,这股敌意简直势不可当。或许乔姆斯基可以在麻省理工学院当一名语言学教授,或许语言学可以在那里被列入人文学科,但乔姆斯基的研究是科学,而科学就是大写的敌人——每个实名认证的人文主义者都知道这一点。
自然带来的知识无不可爱,
我们的智力贸然插手,
扭曲了万物的美好形态,
——我们杀戮,以解剖
华兹华斯的浪漫主义观点认为,科学家是美的谋杀者,而这一点似乎完美地体现在了诺姆·乔姆斯基、自动机理论家和无线电工程师身上。但一个天大的讽刺在于,乔姆斯基一直都在捍卫一种对待科学的态度,而这种态度似乎可以给人文主义者带来救赎。正如我们在上一节所看到的,乔姆斯基认为科学是有限度的,尤其是当它遇到心灵的时候,就像是踢到了铁板。要把这件怪事辨个分明,一直都挺难的,即便对于那些能够处理当代语言学中的技术性细节和争议的人来说也是如此,不过这件怪事也确实令人讶异很久了。乔姆斯基抨击B.F.斯金纳《言语行为》(Skinner, 1957)的那篇评论(Chomsky, 1959)广为人知,是认知科学的奠基性文献之一。与此同时,乔姆斯基一直坚定不移地敌视人工智能,并且大胆地将他的一本主要著作命名为《笛卡儿语言学》(Chomsky, 1966)——仿佛是在认为笛卡儿的反唯物主义二元论就要卷土重来了。他到底站在哪一边呢?反正不是达尔文那边。如果畏惧达尔文者想找一位本身就颇具科学渊源和科学影响力的勇者,乔姆斯基就是他们的不二之选。
我当然是慢慢才明白这一点的。1978年3月,我在塔夫茨大学操办了一场引人注目的讨论会,而哲学与心理学学会(Society for Philosophy and Psychology)顺理成章地承担了主办方的职责。有一场小组讨论名义上是要谈人工智能的基础和前景,结果却变成了四位重量级理论家之间的口舌之争,宛如一场双打摔跤赛。诺姆·乔姆斯基和杰里·福多尔向人工智能发起攻击,罗杰·尚克(Roger Schank)和特里·威诺格拉德(Terry Winograd)则挺身护之。
尚克当时正在研究用于理解自然语言的程序,两位批评者的火力集中在他的一个方案上,该方案旨在(在计算机中)对由某些细枝末节组成的杂乱无章的集合加以表征,这些细枝末节尽人皆知,而且也是人人在解码寻常言语行为时都要依靠的,而寻常语言行为往往是暗示性的、不完整的。乔姆斯基和福多尔对这项事业大为不屑,但他们发动攻击的根据却随着比赛的进行而渐渐起了变化,这是因为尚克在霸凌成风的院系里也是一把好手,他坚定地捍卫着自己的研究项目。他们一开始的攻击策略,是对准概念上的错误进行直截了当、“第一原理”式的谴责——尚克的研究不是竹篮打水,就是水中捞月——可最后乔姆斯基却做出惊人的让步:事实可能确如尚克所料,人类理解对话的能力(以及更一般意义上进行思考的能力)可以用成百上千个粗制滥造的小装置之间的互动来加以解释——但那就太跌份儿了,因为那会最终证明心理学并不“有趣”。在乔姆斯基的心目中,只有两种可能性是有趣的:我们最后可能发现心理学“就像物理学一样”——其规律性可以被解释为若干深刻、优雅、不可抗拒的法则造成的结果——或者,我们最后可能发现心理学全然没有法则——在这种情况下,研究或阐明心理学的唯一方法,就会是小说家的方法(假如真是这么回事儿,那么比起罗杰·尚克,乔姆斯基肯定更喜欢简·奥斯汀)。
随后,讨论组成员和观众之间也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乔姆斯基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同事马文·明斯基的一项观察将争论推向高潮。“我想只有麻省理工学院的人文教授才会对第三种‘有趣’的可能性如此习焉不察:我们到头来可能发现心理学就像工程学一样。”明斯基一语中的。用工程学方法来考察心灵问题,其前景中的某些东西正是一类特定的人文主义者所深恶痛绝的,而且跟讨厌唯物主义或讨厌科学无关。乔姆斯基本人就是一个科学家,而且想必也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他的“笛卡儿式”语言学走得并没有那么远!),但他不会跟工程学产生任何瓜葛。心灵若只是一个小器具或小器具的集合,总归有损于其尊严。心灵就算最终被证明是一个无法破解的奥秘,一个专供混乱栖身的秘所,也好过成为那种会把自己的秘密拱手交与工程学分析的实体!
虽然明斯基对乔姆斯基的观察当时打动了我,但我并未领会个中要旨。1980年,乔姆斯基在《行为与脑科学》上发表了作为标靶文章(target article)的《规则与表征》(Chomsky, 1980),而我则是评论者之一。不管当时还是现在,争议的焦点都在于,乔姆斯基坚持认为,语言能力在很大程度上是先天的,而说孩子会习得语言能力则是不恰当的。按照乔姆斯基的看法,语言结构大体上是以先天指定规则的形式固定下来的,孩子所做的不过是设定一些相对次要的“转换开关”,这些开关的作用在于把他变成一个讲英语而非讲汉语的人。
乔姆斯基说,孩子不是一种通用学习者——用纽厄尔和西蒙的说法就是“通用问题解决器”——不是必须弄清楚什么是语言,然后学习如何进行语言活动。与此不同,孩子先天具有说语言、理解语言的设备,他们只需要排除一定的(非常有限的)可能性,并且采纳一定的其他可能性。按照乔姆斯基的看法,这就为什么连“慢半拍的”孩子学起说话来也是毫不费力的。他们压根不是真的在学习,顶多就像鸟类学习振翅那样。语言,还有翅膀,只在注定会拥有它们的物种身上发育发展,而对于缺少相应的先天设备的物种来说,它们则是无从企及的东西。若干发展诱因会启动语言习得过程,随后若干环境条件会进行一些次要的修剪或塑形,孩子遇到的是哪门语言,母语就是什么。
这一主张受到了强烈抵制,但我们现在可以确定的是,真相离乔姆斯基较近,离他的反对者们则较远。(详见Jackendof,1993和Pinker,1994中为乔姆斯基立场所做的辩护。)为什么会有人抵制呢?我在网络论坛上的评论——我在那里提出的是建设性的观察,而不是反对意见——中指出,有一个抵制理由是完全合理的,即使这个理由只是一个合理的希望。先前,生物学家们抵制过“霍伊尔的疯吼”,这种假说认为,生命并不始于地球,而是始于别处,然后迁移到了地球;与此相似,面对乔姆斯基的挑战,参与抵制的心理学家们拿出了一个温和的解释:假如乔姆斯基是正确的,那只会让关于语言和语言习得现象的考察变得难上加难。我们的工作不再是发现近在眼前的、个体儿童的学习过程,这是个我们能够加以研究和操控的过程;我们将不得不“把担子甩给生物学”,希望生物学家可以解释我们这个物种是如何“习得”与生俱来的语言能力的。这是一个更难驾驭的研究项目。依照霍伊尔的假说,人们可以想象:
有些论述会限定变异和选择的最大速率,进而表明并没有足够的时间让整个过程都发生在地球上。 乔姆斯基的论述与此类似,他的出发点是刺激因素和语言习得速度的不足;他的这些论述旨在表明,婴儿身上必定有着大量的天赋设计,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这种成熟能力的快速发展。有一种假设可以带给我们些许安慰,那就是我们有朝一日或许能够通过对神经系统的直接检查,来确认这些先天结构的存在(如同发现了我们那些地外祖先的化石)。但这样我们就必须接受一个令人灰心的结论:学习理论(这里是指它的最一般形式,即尝试解释从全然无知到知识的转变过程)有一个大到出乎我们意料的部分并不属于心理学的领域,而是最有可能属于演化生物学的领域。(Dennett,1980)
令我惊讶的是,乔姆斯基没有看出我这篇评论的用意。虽然他本人已经对什么会让心理学“有趣”这件事有所反思,但他没有注意到的是,当心理学家发现自己可能会把担子甩给生物学的时候,他们可能会因为某件事而“灰心”。多年以后,我终于认识到,他之所以没明白我的用意,是因为尽管他坚持认为“语言器官”是先天的,但这对他来说并不意味着“语言器官”是自然选择的产物!或者说,这至少不意味着可以准许生物学家们挑起这个担子,进而分析我们祖先所处的环境怎样在无比漫长的时间里使语言器官的设计成形。乔姆斯基认为,语言器官不是一个适应现象,而是……一个奥秘,或者说是一个有前途的怪胎。有朝一日,阐明这样一个东西的或许会是物理学,但不会是生物学。
在某个久远的时期可能发生了一次突变,产生出一种离散的无限性,个中原因也许跟细胞生物学有关,能够对此加以解释的物理机制属性我们目前还不知道……它演化发展的其他方面很可能再一次反映了某些物理法则的运作,而这些法则正是适用于有一定复杂性的大脑的那些法则。(Chomsky,1988,p.170)
这怎么可能呢?许多语言学家和生物学家都处理过语言演化的难题,他们所使用的正是在其他演化谜题上行之有效的方法,并且得出了结果,或者至少得出了貌似结果的东西。例如,在光谱上最具经验性的一端,神经解剖学家和心理语言学家的研究表明,我们大脑的一些特征是我们现存最近亲缘动物的大脑所缺乏的,这些特征在语言感知和语言生产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关于在过去600万年左右的时间里,我们的支系什么时候、按什么顺序、出于什么原因获得了这些特性,人们众说纷纭;但这些分歧是能在进一步的研究中加以检验的,检验这些分歧就跟处理——比如说——关于始祖鸟是否会飞的分歧差不多。在纯理论的战线上,要是我们放开眼界,就会看到已经有人推导出了一般交流系统的演化条件(例如,Krebs and Dawkins,1984;Zahavi,1987),人们正在用模拟模型和经验试验来探索这些条件所蕴含的意义。
在第7章中,我们看到了一些见解独到的猜测和模型,它们要处理的难题是生命如何凭借自举的方式使自己开始存在,而关于语言的产生所必定经历的过程,也有大量与此类似的机智想法。毫无疑问,语言的起源问题在理论上比生命的起源问题要简单得多;我们可以用来构建答案的、不那么原始的材料可谓类目繁多。我们可能永远无法确认一些相关细节,但要是真能确认,那这就算不得什么奥秘了,充其量只是一点点无可补救的无知而已。某些分外节制的科学家可能舍不得把时间和精力花在这种迂远的演绎推断活动上,但这似乎并不是乔姆斯基的作风。他并不是对这项工作成功的可能性持保留意见,而是对这项工作的论点本身持保留意见。
把[先天语言结构的]这种发展归因于“自然选择”是万无一失的,只要我们认识到这句论断并无根据,认识到它不过是在表达一个信念,即存在某种对这些现象的自然主义解释。(Chomsky,1972,p.97)
其实早就有迹象表明,乔姆斯基对达尔文主义抱有一种不可知论的——乃至是敌对的——态度,但我们中有许多人发现这些迹象并不容易阐释清楚。对一些人来说,他看上去就是个“隐蔽的创造论者”,但这似乎不太可信,特别是因为他得到过斯蒂芬·杰·古尔德的认可。还记得语言学家杰·凯泽(第10章第2节)借助古尔德的术语“拱肩”来描述语言是如何形成的吗?凯泽大概是从他的同事乔姆斯基那里获得这个术语的,乔姆斯基又是从古尔德那里获得的;古尔德热切地赞同乔姆斯基的观点,即语言其实并非演化而来,而是突然到来的,是一种无法解释的天赋,顶多是人类大脑增大带来的副产品。
是的,大脑在自然选择下变大了。但正是大脑尺寸的增加,以及与之相伴的神经密度和神经连接度,让人类大脑可以施展一系列跟脑体积增大的初始原因完全无关的、范围甚广的功能。不是由于大脑变大了,所以我们才能够阅读、书写、计算,或划分季节——可我们知道,人类文化有赖于这类技能……语言的普遍特性与自然界中的任何其他事物是如此不同,它们的结构是如此奇特,这似乎表明它们的起源是大脑能力增强的一个顺带结果,而不是跟祖先的嘟囔声和手势有着延续关系的一次简单进步。(这个关于语言的论点绝非我的原创,不过我完全赞同它;以上推论思路直接遵循了诺姆·乔姆斯基的普遍语法理论,是从演化角度对他理论的解读。)(Gould,1989b,p.14)
古尔德强调,大脑成长的最初原因可能并不是对语言的选择(甚至不是对更高智能的选择),人类语言的发生发展可能并不是“跟祖先的嘟囔声和手势有着延续关系的一次简单进步”,但这些猜测(出于论述需要,我们可以姑且承认他的这些猜测)并不能说明语言器官不是一种适应现象。就算我们承认它是一种扩展适应,但扩展适应也是适应。就算人科大脑的显著成长在古尔德和凯泽所希望的随便什么意义上是一种“拱肩”,语言器官也仍然会像鸟类的翅膀一样是一种适应现象!不论在设计空间中把我们的祖先硬生生推向右边的那次间断来得有多突然,这仍是自然选择压力下一个渐进的设计发展过程——除非这确实是一个奇迹,一个有前途的怪胎。
简而言之,古尔德把乔姆斯基的普遍语法理论誉为一座堡垒,说它抵御了关于语言的适应论解释,而乔姆斯基也认可古尔德的反适应论,拿它当作权威借口来拒绝一项明摆着的责任,即为普遍语法的先天存在寻求演化解释;尽管如此,这两位权威也只是在一道深渊上彼此支撑罢了。
1989年12月,麻省理工学院的心理语言学家斯蒂芬·平克和他的研究生保罗·布卢姆在麻省理工学院认知科学研讨会(the Cognitive Science Colloquium at MIT)上宣读了一篇题为《自然语言和自然选择》的论文。这篇后来作为标靶文章刊登在《行为与脑科学》上的论文,是他们下的一封战书:
很多人认为,人类语言能力的演化不能用达尔文式的自然选择来解释。乔姆斯基和古尔德就曾指出,语言的演化可能是一种副产品,产生于对其他能力的选择,它还可能是迄今未知的成长法则和形式法则的结果……我们的结论是,完全有理由相信,语法的特化演化是按照一种常规的新达尔文式过程进行的。(Pinker and Bloom,1990,p.707)
“在某种意义上,”平克和布卢姆说,“我们的目标无聊透顶。我们只是要论证,语言与回声定位、立体视觉之类的其他复杂能力没什么不同,而解释这样一类能力之起源的唯一方法,就是自然选择理论。”(Pinker and Bloom,1990,p.708)他们得出这个“无聊透顶”的结论,靠的是耐心评估针对各方面现象的不同分析,这些分析无可置疑——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并表明“语言器官”的许多最为有趣的属性,肯定是由演化产生的适应现象,而这正是新达尔文派所期望的。
不过,麻省理工学院的听众反应可一点都不无聊。根据事先安排,乔姆斯基和古尔德要做出回应,所以现场来者甚众,大家挤得只能站着。名声在外的认知科学家们,在那个场合没羞没臊地表达出对于演化的高度敌意与无知,令我大受震撼。(事实上,正是对那次会议的反思才让我下定决心:必须马上写这本书,不能再拖了。)据我所知,虽然那次会议没有留下记录(网络论坛上的评论涵盖了这次会议提出的一些主题),但如果你想回味一下当时的情况,可以品一品平克列出的(私下交流)最令人叫绝的十大反对意见,这些反对意见都是自论文草稿开始流传以来他和布卢姆对付过的。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在麻省理工学院的会议上,这些反对意见大都以不同的版本出现过:
(1)色觉没有任何功能——我们可以靠强度差异来区分红苹果和绿苹果。 (2)语言根本不是为了交流而设计的:它不像手表,它像一个中间有根棍子的鲁布·戈德堡装置,你可以把它当日晷用。 (3)关于语言具有功能性的任何论证,都可以拿来论证“在沙子上写字”具有功能性,而且论证的可信度和力度保持不变。 (4)要解释细胞的结构,就得靠物理学,而不是靠演化论。 (5)拥有眼睛和拥有质量这两件事都需要同一类型的解释,因为就像眼睛会让你看得见一样,质量会防止你飘浮至太空。 (6)关于昆虫翅膀的那档子事儿不是已经把达尔文给驳倒了吗? (7)语言不可能有用——它引发过战争。 (8)自然选择是无关紧要的,因为我们现在有混沌理论。 (9)语言不可能是经由对于交流的选择压力而演化出来的,因为我们在询问他人感受的时候,可以并不真的想要知道他们的感受是什么。 (10)大家都同意,自然选择对心灵的起源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它又无法解释每个方面——那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古尔德和乔姆斯基对他们某些支持者的奇怪信念是否负有责任呢?这个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平克列出的条目多半都可以在古尔德的主张(特别是2号、6号和9号)和乔姆斯基的主张(特别是4号、5号和10号)中明确找到它们的先祖。那些抱有这些主张(还包括清单上的其他主张)的人,在表达它们的时候通常都会借助古尔德和乔姆斯基的权威(例如,参见Otero,1990)。正如平克和布卢姆所说(Pinker and Bloom,1990,p.708),“诺姆·乔姆斯基,世界上最伟大的语言学家,以及斯蒂芬·杰·古尔德,世界上最著名的演化理论家,这二位一再表示语言可能不是自然选择的产物”。此外——两条关键的狗还未吠出声呢——我还没见到古尔德或乔姆斯基去尝试纠正激战中冒出来的这些疯吼。(如我们所见,这是每个人都会有的弱点;令我感到遗憾的是,社会生物学家们的受困心态让他们忽略了——至少是使得他们疏于去纠正——他们阵营中某些成员那为数不少且糟糕透顶的推论。)
作为达尔文最热情的支持者之一,赫伯特·斯宾塞是“适者生存”这句话的创造者,是达尔文某些最佳思想的重要澄清者,但同时也是社会达尔文主义之父。社会达尔文主义是一种对达尔文式思维的可憎误用,它捍卫的是从冷酷无情到十恶不赦的一系列政治学说。斯宾塞误用了达尔文的观点,达尔文本人对此是否负有责任呢?人们莫衷一是。就我而言,我虽能谅解达尔文没有像真正的英雄那样公开责备自己的拥护者,不过还是遗憾于他私下没能更积极地对其加以劝阻或纠正。
古尔德和乔姆斯基都踊跃支持一个观点:对于知识分子工作成果的运用和可能的错误运用,知识分子本人是负有责任的。所以,当发现自己被这些无稽之谈引以为据的时候,可以想见他们至少会有些尴尬,因为他们自己并不抱有这些观点。(指望他们会感激我替他们做了这些脏活儿,也许是想太多了。)
“后ChatGPT”读书会启动
推荐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