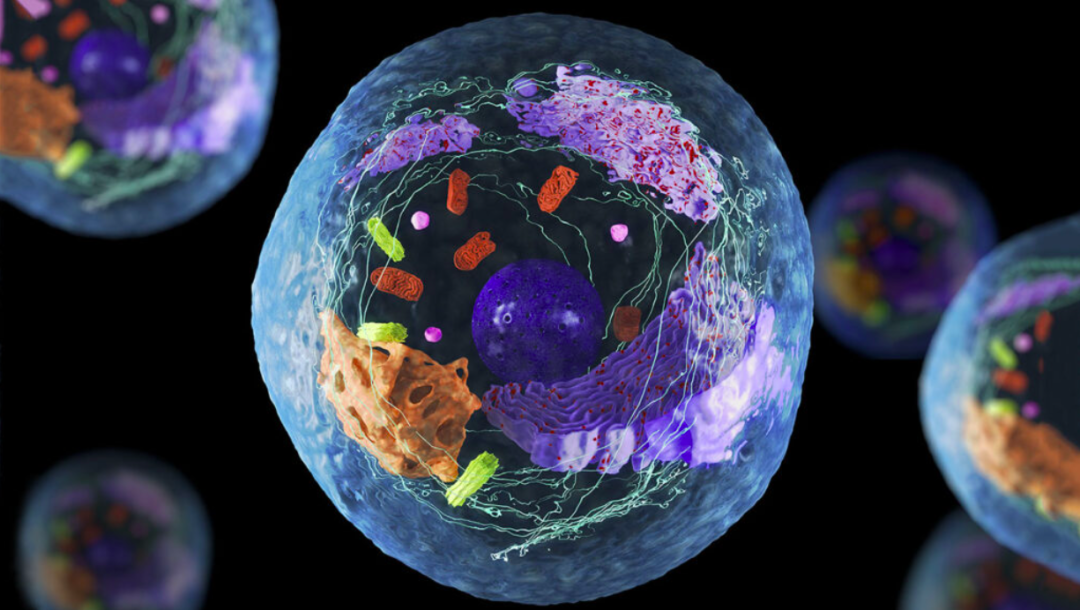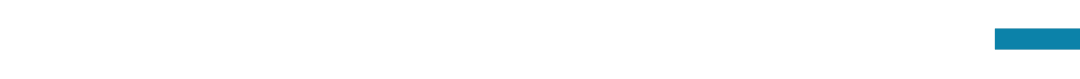摘要
1. 引言
2. 人工是否模仿自然
3. 人工(智能)的边界科学
4. 人工生物学(An Artificial Biology)
5. 人工的新定义
6. 总结
A New Definition of “Artificial” for Two Artificial Sciences
https://link.springer.com/article/10.1007/s10699-021-09799-w
人工智能(artifcial intelligence)和合成生物学(synthetic biology)是两个领域,涉及到新的技术、新的实验方法和新的理论框架,它们都需要一个新的、更具体、更精细的对“人工”(artificial)的定义。这个定义与使用合成方法在开放式(真实或虚拟)环境中构建显示实体相关。需要重新定义“人工”的原因,在于人工智能和合成生物学与生物学本身有着密切的关系。
它们两者都是工程科学,看起来朝着(自然)生物学的方向越来越接近,尽管从不同而相反的方向。我们展示了如何从工程学和合成的角度对生物学进行新的观察,从而得到了“人工”的新概念。在新概念中,自然和人工之间的界线变得更加模糊。基于此,我们试图为未来对这两门人工科学的理解、实践和认识论目的,制定一个全新的、更有用的定义。
特定科学(Special sciences)从不同的角度对人类整体知识提出挑战。它们通过增加总体知识来解决特定领域的具体问题,总体知识包括科学知识和与日常生活相关的常识知识。这引发了关于不同学科之间关系的概念框架的新理论问题。这个方面引发了许多典型的问题,在过去一个世纪里,科学哲学已经从一般的科学哲学变成了特定科学哲学,并且这些概念问题也在不断增加,因为特定科学的数量增多,比如医学哲学、认知科学或工程科学已成为更经典的物理学、生物学或数学哲学的补充领域。
在本文中,我将探讨涉及多个科学领域框架的一个概念问题:自然与人工之间的区别,这是科学思想史上一个持久的话题,从古代哲学开始。我的观点是,传统的“人工”的定义不再适用于描述一些现代人工科学,因为自然与人工之间的界限不再像过去那样清晰明确。我认为,一些具备新技术、新实验方法和新理论框架的新科学需要一个新的、更具体和更精细的“人工”定义来使用。
我特别提到了人工智能(AI)和合成生物学,这是两个相对较新的学科,利用合成方法来构建现实世界的实体,并在开放的(真实或虚拟的)环境中进行研究。重新定义“人工”的必要性源于人工智能和合成生物学与生物学之间的紧密关系。它们都是工程科学,在不同且在某种意义上相反的方向上趋近于(自然)生物学。然而,有趣的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人工智能和合成生物学朝向自然生物学的发展突显了这两门科学与生物学本身的巨大差距,以及它们在“人工”性质中与生命存在的自然世界之间的距离。因此,“人工”的新概念是一种从工程和合成观点对生物学进行新视角的结果,其中自然与人工之间的界限更加模糊,也是由于这种双重情况的结果。
在思想的历史中,我们可以找到类似的情况,就像Leibniz试图定义人工和自然机器之间的区别一样,后者保留了机器的最小部分,根据Leibniz本人有争议的说法(Nachtomy,2011)。在讨论这个复杂的主题时,Leibniz根据他对自然机器的定义,将区别归结为聚合体和统一体之间的差异,这与他的形而上学观点相吻合。关于Leibniz关于自然机器概念的长期争论不是本文的范围,但Leibniz的尝试表明了在一个主要是在生物学出现之前的时代,从“自然”观点(例如自然机器的观点)关注人工与自然之间的区别的兴趣,以及对这些观念处理的困难。【1】
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将探讨人工智能和合成生物学中关于人工性的问题。在第2节中,我将重点关注人工的古老概念,即模仿自然以及化学和人工科学中出现的一些当代变化。在第3节中,我将讨论人工智能及其在生物学中的方面,特别是最近的方法和技术。在第4节中,我将探讨合成生物学的人工性。然后在第5节中,我将尝试阐述一个新的、更具体的人工定义,我称之为“Artificial”,并在第6节中得出一些结论。
虽然远没有拥有一个明确且一劳永逸的自然与人工之间的明确定义,但我们对此有直观的概念。我们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但详细描述这种区别是困难的。事情如此的原因很可能与文化演变以及我们与自然、知识和科学的关系变化有关。然而,这种区别不仅仅是为了满足文化的需要。它确实关系到并影响着我们对现实的看法,以及对特定科学和技术成果的态度。因此,自然与人工之间的区别是我们研究和科学活动的必要部分,因为它为不同的科学领域建立了对象,并提供了研究所关注领域的方法和方法论。这一点一直存在。每个时期都有其自己关于自然和人工的概念,它塑造了科学和技术的形式和关系。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自然和人工之间的关系可以被描述为一种演变的极化(evolving polarity,Bensaude-Vincent&Newman,2007),而如今的学科,如计算机科学和生物技术,迫使我们重新评估这个区别,无论是关于它的概念(源自以前的时期)还是关于自然和人工的常识观点。我们可以说,和许多其他极性关系一样,它应该被视为一种程度上的区别,而不是非黑即白的区别。然而,问题并不那么简单,因为对于在医学、生物学、健康、法律、政治和伦理等特定情况下的需要,对于明确区分的要求是由于在具体情况下做出的决策。对于什么是人工的,什么是自然的清晰定义是一个认识论问题,它应该综合考虑科学、社会和人文等各个方面。对于两个学科,人工智能和合成生物学,它们很好地结合了科学、技术和人文特质,这一点尤为真实。
在《物理学》的某些段落中,亚里士多德区分了两种艺术形式,即艺术是人类创造的,与自然形成对比(实际上,“人工”一词的词源就是如此)。亚里士多德提到的这两种艺术形式是:(1)模仿自然的艺术;和(2)通过逐步实现特定自然情景的完美状态的艺术,比如医生的例子【2】。这种区分很有趣,并遵循了亚里士多德对“人工”的更常见的定义,即人类能够将某种自然现象赋予一种形式和结构的能力。例如,利用一些从自然界中获得的材料来制作某种物品,而这些材料本身没有固有的改变动力。【3】这第二个定义是众所周知的,似乎更适合谈论人工智能和合成生物学时的人工和自然之间的关系。
一方面,在人工智能的起步阶段,模仿在其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当图灵最初谈论对人类智能的模仿时,他通过编程实现了一台能够下棋的纸带机(Turing, 1948)。其次,他通过与一种更复杂的机器,即数字计算机,进行更复杂的语言互动来谈论人工智能的模仿(Turing, 1950)。在这两种情况下,机器必须通过放弃其他人类的、更具身体性的能力来模仿人类智能。另一方面,在人工智能的其他领域,如机器人技术、类人机器人技术和虚拟人技术中,模仿和相似性都至关重要。
例如不可思议的谷理论(valley hypothesis,Mori,1970年),建立在人类和机器人之间相似性的概念上。机器人越多地模仿人类,人类与机器人之间的亲近感就越强,但这仅仅是该理论的第一部分。该理论的核心部分指出,在描述人工人形制品与人类之间不断增长的相似性曲线上,存在一个范围,即“不可思议的谷”,在这个范围内,由于人形特征的增加,人类与人形制品之间的情感联系被大大削弱。超过这个范围后,人类对人形制品的情感转化为舒适的情感。有许多不同的阐释来解释这种现象【4】,但与模仿相关的一个关键问题是:曲线的最高点,超过了不可思议的谷,对应于一个健康的人。这不可能是一个除了理想化概念之外的人类;然而,它是一个比大多数其他人更像人类的完美人(Dumouchel&Damiano,2017年)。这一点共同回忆起亚里士多德在《物理学》第二卷第8章中关于人工的两个方面的定义。完美的相似性消除了不可思议,使其消失,这引发了关于人工智能和合成生物学中自然和人工之间关系的问题,其中人工是对自然的模仿。例如,可以提出以下问题:模仿到什么程度定义了人工性?在何种程度上,相似性或复制的界限超过了人工成为自然的物体?这个界限在理论上和技术上是否可以到达?这些问题引发了进一步的哲学研究,如下:自然和人工之间的区别对人类来说有多可怕?如果是这样,这与特定学科的关系如何,特别是那些致力于复制人类某些方面或整体的学科,如人工智能和合成生物学?对这些学科内的研究有何影响?对其特定对象的定义有何影响?对科学研究以及社会的伦理或法律后果是什么?所有这些问题都与处于人工和自然边界的学科的科学研究核心相关,并且试图从人工出发达到自然状态。”
尽管模仿不是人工的普遍特征,但它也存在于与生物世界更相关的学科中。例如,自19世纪以来,化学领域一直在尝试生产仅由其他生物产生的物质(Brooke, 2007),其中许多成功的尝试导致了有机化学的建立。无机化学的发展在合成各种塑料等化合物的过程改进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这种改进使得“合成”可以被视为“人工”的同义词(Bensaude-Vincent, 2007)。合成的一般方法论作为创建新化合物、材料和由生物产生的物质的方法,已成为通往与我们当今观念更一致的人工新领域的重要一步。然而,合成方法本身带有人工的两重特性:(1)对某物的模仿;和(2)通过(重新)组合、转化或再创造自然元素或产品来创造出一种改进的东西。
所有这些活动通常被视为仿生学和更广泛的生物启发技术的范畴。有趣的是,仿生学或生物模仿在合成生物学中是一个相关的部分(Church&Regis,2012)。从这个观点来看,合成生物学可以被视为从化合物合成的概念到生命合成的路径的终点。然而,在合成生物学中,生物材料或化学物质构成了生物系统的基础,生物材料的合成并不仅仅是对自然界的模仿,同时也是对新生物设备、部件和整体系统的创造。自然和人造之间的区分变得模糊。在谈论生物合成产品时,我们在哪里划定界限?什么是我们定义为自然的,什么是人造的?专利制度所使用的规则可能设定了一种常规的界限(Bensaude-Vincent,2007),但它们对于认识论和研究目标来说过于狭隘。
我在这篇文章中首先提出的观点是,人工智能(AI)和合成生物学是互补的学科,并且从人工的角度来看它们是相互关联的。我们将逐一探究这两个领域在多大程度上重叠,并在哪些方面存在关联。首先,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人工智能,包括其定义、目标和范围。然后,我们将探讨人工智能的“人工性”。接下来,我将以类似的方式探讨合成生物学,并确定其具体而独特的“人工性”。
人工智能(AI)的确切定义很难达成,因为它在视角、目标、对象和方法上经历了很多变化。对于AI的人工性质也是如此。在一本知名的人工智能教科书的第三版中(Russell & Norvig, 2009)【5】,他们列举了八个人工智能的定义和两个维度,如下所示:(1)推理和行为,以及(2)人类表现和理性表现。第一个维度涉及了思维过程和“思维规律”之间的区别,以及智能行动之间的区别。这是认知人工智能和工程人工智能之间的传统区别。第二个维度更有趣,因为它强调了以下两者的区别:人工智能作为实际智能人类表现的模仿,和最终目标是实现理想的智能(特定或普遍)表现,符合“完美”理性的观念【6】。这是又一次人工性的自然模仿和对自然事物改进之间的区别。在人工智能领域,这两种不同的观念特别明显。这四种情况只是一种抽象,但它们几乎包含了相关文献中的每个立场。然而,这种区别基本上是基于两个“自然”概念:1)人的本质;2)理性的本质。换句话说,它并不关注人工性。这通常是人工智能定义的主流,因为“AI”标签的核心更多地是智能(人类和/或智能系统的智能),而不是人工性。【7】
在《人工的发现》(The Discovery of the Artifcial)中,科迪什(Cordeschi)认为,人工智能的两个主要倾向从该学科的开始就存在,并强调它们与“启发式”(heuristics)这个术语的两种不同用法相关。在第一种意义上,这个术语指的是“尽可能详细地模拟人类认知过程”;而在另一种意义上,这个术语指的是“通过允许通常非人类的过程(例如计算机擅长的过程),获得尽可能高效的程序性能”的可能性(Cordeschi,2002: 190)。如果我们将启发式视为以人类或非人类方式实现智能的所有方法的最一般性描述,这种特征将智能的重点转移到了人工性上。这两种人工智能倾向之间的紧张关系在文献和研究中已有很长的历史,这种关系在当代人工智能方法中仍然存在。
然而,对于启发式的强调印证了这样一种观点:人工智能中的人工不仅仅是计算机上的模拟,而是通过计算机模拟一种方法和过程,允许创造出一种通过绕过蛮力编程的计算限制而被定义为智能的东西。这些方法和过程是否与人类使用的方法相同并不重要。这在以前和现在对通过应用人工智能方法来研究和理解人类认知感兴趣的研究人员来说可能很重要。人工智能中的人工问题早在早期的研究中就出现了,作为一个软件问题而不是硬件问题,尽管正如科迪什指出的,启发式和对启发式的实验“很快就转向其他与状态空间中的选择性搜索不同的方向”,而状态空间是自动问题解决中的一个标准,“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建议、项目和实验”(Cordeschi,2002: 191)。同样重要的是,“以启发式为导向”的人工智能方法是综合方法的主要核心,它是一种建立模型的方法,构建具有有机体共享原则的人造品——这些人造品“不仅仅是模仿生物行为”(Cordeschi,2002: 248)。
合成方法的根本目的是测试和验证生物体行为理论,从感觉运动到高层次认知方面。根据这种方法,构建一个人工制品并分析其行为,以查看控制该人工制品的机制是否在某些方面与控制其所启发的生物系统的机制相同。这对硬件人工制品(如机器人)和软件人工制品(如智能系统、AI经典程序、神经网络甚至硬件人工制品的计算机模拟,如机器人计算机模拟)都是有效的(Datteri & Tamburrini,2007;Cordeschi,2008)。在合成方法的意义上,合成人工制品必须具有一些特定的约束条件,才能将其视为理论或理论部分的模型,用于解释行为。只有当约束条件相关且对于使人工制品在某种意义上成为其模型系统的模型时有用时,合成方法才能验证、证实或拒绝构建该人工制品的理论。合成一个人工制品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选择用于建模生物系统(其行为应该被解释)的约束条件。【8】与生物系统的联系是AI的控制论根源的结果,但它也与与生物系统通过自治和生存概念相连的智能感有关,这些概念在AI多样化发展中越来越重要。不可能进一步分析智能概念——事实上,在AI哲学和AI总体上这是一个长期辩论——因为本文的重点是AI的人造性。
尽管合成方法被认为是支持模拟人类认知过程的人工智能趋势的最佳选择,通过允许使用具有相关约束的计算机模拟作为认知模型,但这种方法不仅限于这种倾向或仅模拟传统的认知能力,如(抽象的)推理、问题解决或记忆检索。在过去的40年中,人工智能从理论和应用的角度已成为广泛而多样的研究领域。如今,机器学习、神经网络、非人形和人形机器人、深度学习、搜索优化算法、语音助手,甚至物联网都属于人工智能的范畴。对人类认知建模和智能行为中的高效人造品和系统的研究仍然是人工智能产品的两个普遍分类。除了前述内容之外,尽管计算机模拟——即人工智能的软件方面,在理解人类思维或认知世界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Weisberg,2013),但人工智能的硬件方面也再次变得重要,就像人工智能诞生之前的控制论时期一样。这并不意味着人工智能人造品的硬件方面不能被模拟,事实上,在虚拟机器人技术、机器人模拟工具或多智能体系统的虚拟环境中它们已经被模拟了(Shoham&Leyton-Brown,2009)。然而,最近的一些具体的、嵌入式的、环境化的和硬件方面的人工智能趋势表明生物学对人工智能产生了更大和更彻底的影响。
谈到生物学AI(biological AI),这种影响不仅可以在被称为人工生命或ALife(Artifcial Life,Aguilar等人,2014)的AI的大部分中识别出来,它专门致力于通过计算机模拟和机器人研究生物系统和自然生命。【9】生物学对AI的影响导致了在某些层面上具有可识别为生物学特征的系统的创建。这些例子包括神经网络、演化算法、元胞自动机和所有生物启发AI系统(Floreano & Mattiussi,2008)。在这些方法中,有一个值得特别提及的方法涉及生物(神经)组织与硅电路之间的集成:神经形态计算(neuromorphic computing)。从Carver Mead(1990)关于神经形态电子系统的开创性研究开始,这种方法展示了一种新方向的基于神经网络的AI方法,它与神经元的生物学有更深层次的类比。神经形态计算和工程学的目标是重建人脑结构和神经元功能,以确定系统如何应对现实世界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新技术,如脉冲神经网络(Spiking Neural Networks),它通过单个神经元在达到阈值时传输信息的功能(Wulfram & Werner,2002),旨在以更详细的方式复制和模仿大脑功能。这种趋势在过去几十年中一直在增长,许多项目都通过神经形态工程进行了计算模拟大脑;例如欧洲人脑计划。创建电路以绕过数字软件神经模拟(Poon & Zhou,2011)通过模拟到神经硅芯片,是由“越是生物学,我们得到越好的人工”这一想法指导的,因为生物信息处理比传统数字方法更有效【10】,尽管与人类认知水平之间仍然存在差距。
相反,AI的生物学灵感并不是一个容易解决的问题。例如,生物启发AI(bio-inspired AI)的核心概念——具身(embodiment)问题——存在争议;可以说,“具身”的含义并不清楚。如果“具身”仅指感觉运动认知方法,即智能体与物理或社会世界之间的感觉运动交互,那么它将认知根基于感觉运动交互,并与激进的认知科学方法相关(Chemero,2009)。这种方法似乎缺乏更具体的生物学特征,它与生物自我调节机制的联系(Ziemke,2016),以及从稳态角度看典型的生物系统的组织性质。毫不奇怪,这在机器人领域是一个大问题:机器人的身体与生物身体有多大程度的相似性?为了达到一个合适的自然系统模型,机器人身体需要多大程度的生物性质?以及建立一个自治系统?【11】一个关键点涉及AI生物学灵感的可实现可能性。Damiano和Stano(2018)强调,在标准具身方法中只有生物系统和过程的表面方面被重构,因此有必要转变视角,采用一种能够在合成建模中使用生物组织来减少自然与人工之间距离的不同方法。这种距离突显了AI向生物学推进更具问题性,和自然与人工之间的困难边界。
AI生物化的不同方面已经表明,到目前为止,它们已经产生了新的方法或尝试,以及许多一般的理论、方法论和认识论问题。这些问题部分涉及AI的“人工”。例如,如果软件或硬件人工制品类似于自然实体,那么人工模型与自然实体本身之间的界限在哪里?如果重要的是人工模型的约束条件,而这些约束条件只有在它们使实体成为生物实体时才相关,那么自然与人工之间的区别在哪里?一个人工制品在多大程度上不再是人工的而变成了生物意义上的自然?大概,这样的问题需要一个更好、更新的AI人造性定义,出于理论、伦理、方法论和应用原因,因为通常用来回答它们的概念,如功能主义多重实现;生物或非生物基质、信息处理和编程与进化目前太狭窄和模糊,无法像以前那样继续使用它们,在AI的视角下,当时生物学和AI更加彼此远离。
4. 人工生物学(An Artificial Biology)
合成生物学的概念并非新鲜事物。如前所述,合成生物学是一门学科,具有不同的目标、方法和范围,这些目标、方法和范围是在过去30年里不同的技术和科学成就的结果。从时间上看,第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是人类基因组计划的成功,该计划绘制了整个人类基因组图谱。实际绘制每个生物的基因组的可能性迅速提出了一个可能性,即为一个生物甚至是尚不存在于自然界中的生物,构建部分或整个基因组。创造基因组的道路从病毒基因组转向细菌基因组,目标是构建一个完全合成的有自主生存能力的生物体。通过使用与自然界中的进化发展系统相同的材料(DNA)来创造生命系统的基础,催生出一种全新的人工特性和新型机器。这些新的机器不再是非生物的,它们被称为“生物人造品”(biotic artifacts,Preston, 2018),同时是由人类创造的具有自主生命和机械特性的系统。
这种类型的机器在自主行动和在一个开放环境中生存的意义上被称为生命机器(living machines)。实际上,这个开放环境对于其他所有自然系统来说都是自然环境。然而,它们仍然是由人类建造的,人类在这种情况下扮演设计者的角色,尽管他们并非控制者,或者至少很难断定在合成生命系统的情况下,创造者对系统行为具有完全和绝对的控制能力。在这些“机器”的情况下,人工和自然之间的界限问题再次出现。自然与人工之间的边界在哪里?对于这些生物人造品来说,我们如何定义自然和人工?对于这些问题,并没有简单的答案,至少在传统的“人工”和“自然”的用法上是如此。合成生物学的这一部分使得这些问题变得尴尬。例如,如果唯一的区别不在于它们的材料或行为,而仅在于它们的获取方式,即不是通过进化过程而是通过实验室过程获得,那么很难不将这些实体定义为自然实体。这是一个重大的区别,但从自然/人工的二分观点来看,它是否也是一个区别?或者相反,它与这个观点毫无关联?
然而,这只是关于合成生物学的问题的一部分。通过BioBricks构建生物体的部分或整个基因组,将其放入类似的生物体中并开始繁殖,可能引发关于自然与人工之间关系的明确问题。合成生物学中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基因操作和改变,更为人所熟知的是基因组编辑。最著名的编辑技术基于 CRISPR,这是一种在细菌中发现的用于抵抗病毒的防御机制。粗略地说,它们是构成细菌生物化学记忆的DNA序列。对这一机制的理解以及“相关系统”的实施,尤其是Cas9 核酸内切酶,使得基因操作成为可能,包括切割、插入、删除或替代DNA序列,通过对特定和期望目标的DNA断裂(Zhang等,2014年)。Cas9是一种酶,位于cas基因簇中介导目标DNA断裂。
这种技术存在一些问题,例如由于引入新基因或直接修改基因而导致的镶嵌风险或意外突变。最近的进展已经产生了类似的技术,这些技术较少侵入性,因为它们是通过编辑RNA实现的(Katrekar,2019年)。尽管这项技术还很新,并且在未来几年需要进一步改进,但RNA编辑似乎比标准基因治疗更加灵活。它基于一类名为“作用于RNA的腺苷脱氨酶”(ADARs)的酶家族,这些酶更少“侵入性”,因为它们更像是一种覆盖函数,通过在不破坏RNA分子基本结构的情况下在化学上改变字母(Reardon,2020年)。
这两种技术从不同的角度引发了一些问题。涉及的问题包括:在应用过程中对结果的实际控制;在使用它们的生物系统上的后果;对已编辑有机体行为的(不可)预测性;以及编辑有机体引发的影响。这些问题涉及实际、方法论、伦理和认识论等方面,将在未来几年需要解决。关于自然与人工之间的区别的问题对于帮助解决这些问题,引发相关但难以回答的问题非常有用。编辑过的基因组有机体是自然的还是人工的?界限在哪里?通过DNA序列的修改使有机体变得人工吗?如果RNA编辑像预期的那样是一个部分过程的修饰而不是过程的源头,那么一种较少侵入性的方法是否更自然而较少人工?如果是这样,为什么?有什么依据可以将一种事物定义为更人工或更自然?很可能,这些问题因为与更近期学科的基础相关的认识论目标以及实际、伦理和规范目的,需要重新定义人工性和自然性的概念。
合成生物学并不局限于对DNA或RNA的操作,或者从头开始构建DNA并植入自然环境中,比如上面提到的Synthia的例子中所示。合成生物学也涉及从零开始构建活体系统。对这个主题的研究一直专注于完全自下而上的方法,但仍未显示出可实现或显著的结果。例如,合成生物学离拥有足够相似于活体细胞的合成细胞仍然很远,这些细胞并不能自主地自我维持(Stano,2019年)。粗略地说,将构成细胞的所有组成部分放入一个膜内,以获得与活体细胞典型的动态组织相似的结构是困难的(Deplazes&Huppenbauer,2009年)。【14】这凸显了合成生物学相关的另一个潜在困难区别,即自然与人工之间的区别,即生命和非生命物质之间的区别。这一区别非常重要,因为它将问题转移到了更复杂的层面,涉及到创造生命的过程,这是通过构建DNA无法实现的,而是需要构建一个能够解读和“使用”DNA的系统(Deplazes&Huppenbauer,2009年)。【15】
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合成生物学是一个理想的测试候选者,用于测试合成方法的潜力,它是其应用的主要示例。特别是,合成生物学允许对生物可能性进行研究、构建,并具体化“如何可能”的模型(Koskinen,2017年)。通过物质实体具体化“如何可能”的模型的可能性增加了它们的有效性,并使它们以更具体、更少抽象的方式发展,这通常是科学哲学中所指的。【16】通过合成生物学中从“如何可能”模型出发达到的合成模型,在许多情况下是“基于数学/计算模型但有生物学实体,例如基因和蛋白质”(Knuuttila&Loettgers,2013:877);它们通过提供实质性的修改改善了数学/计算模型的使用。数学建模和合成建模的综合应用是合成生物学中合成范式的核心(Sprinzak&Elowitz,2005年),并通过提供更经典的实证实验结果从单纯的“如何可能”模型过渡到相关实体。是什么使这成为可能?使用“正确类型”的物质性(Knuuttila&Loettgers,2013年)。模型即新的生物实体的物质性保证了抽象构思的东西可以通过开发生物现实而成为实际装置,同时合成实体将抽象模型的人工性转移到生物模型中。因此,我们陷入了一种理论困境,如下所示:(1)我们必须承认生物和自然并不相同,不可叠加,而是相当不同;(2)或者我们必须更好地定义生物学世界中的什么是自然的,什么不是自然的。
这些问题涉及合成生物学的主要流派,包括:(a) 对生物系统或其部分的重新设计;以及 (b) 设计和构建新的生物系统或其部分。虽然前一种情况表明,人工性是其自然部分的重组(例如,DNA或RNA片段或蛋白质作为BioBricks),这些自然部分本身就是生物进化的结果,但后一种情况侧重于使用“非自然的分子部分来完成自然生物体完成的功能”,特别是在“化学合成生物学”中(Benner等,2011年:372)。此外,人工性还涉及系统材料中不是生物进化结果的部分。所以,(a) 是人工功能的情况,而(b)是人工物质性的情况;然而,这两种情况都可以被定义为生物学的“人工合成系统”(Koskinen,2017年:499)。在人工和自然之间的界限在经典定义的文献中仍然难以确定。
在关于合成生物学作为一个具体展示多重实现可能性的领域的最近讨论中,生物工程实体被描述为人工生物系统,“与其自然发生的近亲分享许多共同特征,但仍然是具有许多受限特征的人工对象”。这进一步强调了生物性和自然性之间的差异,因为它们是“人工系统,不必满足自然选择对其适应能力施加的严酷要求”(Koskinen,2019年:4-7)。【17】这些系统是自然和非自然DNA碱基的混合物的结果。这样的工程和科学进步正在使自然和人工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
迄今为止,我们看到人工智能(AI)和合成生物学都在快速发展,并与“人工”的概念密切相关,这将它们从相反的方向推向同一个模糊的界限,考虑到它们的“生物性质”。一方面,按照定义,人工智能是一门人工学科,它向生物学靠拢,将其作为构建能够在开放环境中行动的工件的主要目标,不论是模仿亦或是受其启发。相反,合成生物学是一门“工程化生物学”,其中人工性是一种对其单细胞或多细胞系统的非自然材料部分进行操作、重组或插入的问题。它们都使用合成方法构建模型,并将其实现为虚拟或实体。我们还看到,人工智能和合成生物学朝向生物学的发展实际上并不简单。在广义上实现生命和认知——这是当今生物学的两个支柱——即使是在最低限度上,对于这两个学科来说也很困难,无论它们与生物学是疏离还是紧密相关。合成生物学和尤其是人工智能的科学和技术研究的热情不止一次受到挫折。由于对人工智能和合成生物学设立目标的反复调整,以符合现实分析,进一步增加了对人工性的讨论,同时也推动了更好地定义这一概念,以改进这两个与生物学密切相关的领域的理论和应用研究方面的工作。
我将逐步详细阐述并制定一个与自然相关的人工的新定义(称为“Artifcial”),以更好地理解人工智能和合成生物学,并摒弃传统文献中的经典定义。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在理论、实验和方法论等方面实现与人工智能和合成生物学实体相关的更具体的定义,而这也会在伦理、法律、应用和政治等问题上产生副产品,并不可避免地成为未来几年各种公共和私营机构议程中的议题,这些机构对这些领域的研究进行监管。
要制定这个新的“人工”定义,我从最一般和中性的定义开始,即:
很容易看出A1太过一般性,因为有许多人类活动产生的东西通常不被视为人工。例如,散步、交谈或生孩子。因此,我们可以将A1进行细化,如下所示:
这是一个标准的字典定义,将人工的范围限定为由人类以艺术或巧妙的方式形成或创造的事物。【19】这是一个好的定义,因为它涵盖了对自然模型的参考,并不关心它是通过模仿还是灵感开发出来的。然而,对于人工智能和合成生物学来说,这个定义并不够有效和有用,原因有两个。虽然人工智能的一个子领域致力于艺术和创造力(Boden, 2009),但A2中涉及到的“艺术”部分对于整个人工智能的具体定义并不相关(第一个原因)。然而,有人可能合理地争论说,不论是艺术、工程还是实用,某物的设计目的并不拘泥于特定的艺术性,对于我们正在处理的这两个学科来说,人工智能和合成生物学的核心都是一样的。重要的是实现人工事物或实体的过程,而不仅仅是目标本身。
考虑到这一点,第二个原因似乎更为显著:A2过于人类中心。这看起来与直觉相悖,但事实并非如此。尽管人类活动确实是标准、经典定义中人工的核心所在,因此人工被定义为非自然的,并且不是从自然出发,如上面提到的人工智能和合成生物学的例子显示了自主性在人工系统中所起的关键作用。自主性对于在现实世界中产生效果是必要的,它允许系统在开放性的环境中行动、表现和运作,同时保留其动态和不断变化的环境相关变化和响应。如果这是生物系统的典型特征,那么对于合成生物学系统也是一样的,但在人工智能系统中处理自主性更加困难。这个问题在文献中已经被广泛讨论过。【20】忽略掉人工智能自主性的许多问题,为了论证,我将假设自主性是在没有人类控制的情况下进行操作的能力。这将区别于像纯粹的工业机械那样的机器,与用于工业生产的非人形机器人,或者将普通汽车与人工智能汽车区分开来。涵盖这一方面的定义如下:
A3: 人工是人类所构建的事物,通常借鉴自然模型,尽管它可以在没有人类控制的情况下在开放的环境或背景中继续存在、运作和表现。
A3包括了人工智能和合成生物学系统的许多方面,特别是在创造或构建实体/工件的过程中人类的角色至少是存在的。人类的积极作用似乎是将某物归类为人工的必要条件,尽管人工智能和合成生物学实体的区别在于人类的作用必须在某种程度上受到限制,但不能消失。人类的因果作用本质上是人工的一部分。
最后一个问题涉及到本研究所使用的特定实体的物质性质。A3是对于人工智能系统的人工性质的适当定义,因为它将自主性与构建人工智能系统的人类角色联系在一起。A3也适用于每个受生物启发的人工智能系统,无论它与生物(自然或非自然)实体有多么相似,它也是一种限制,用以表征在开放的环境中创造出强大且灵活的人工智能系统的启发法则。然而,对于物质性质又如何?对于由生物的自然或非自然部分组成的人工系统,例如合成生物学中的系统,如何处理?对于创建一个新形式的定义,需要最后一个改进:
A4:人工是人类所构建的事物,通常借鉴自然模型,同时通过对自然系统和过程的操纵,以及在没有人类控制的情况下,在开放的环境或背景中保持现有并继续存在、运作和行为,无论其组成部分的物质或材料如何。
A4是对于“人工”的定义的一个很好的候选,因为与标准定义相比,它更加丰富。此外,这个定义涵盖了人工智能和合成生物学的特定特征,它们以一种渐近的方式越来越接近,前者通过向生物学(实体、方法和过程)的不断灵感迈进,而后者通过在非自然的方式下使用生物学部分,或者在生物遗传背景下使用非自然的部分。
A4并没有解决所有问题,这进一步证实了“人工”概念的演变,由于人工智能和合成生物学的进步,它可能变得更加复杂。例如,由人类构建的人工智能系统所创建的人工智能系统是否仍然是人工的?如果人类的因果作用仍然有效,即使是间接地或以某种方式进行介入,答案是肯定的。换句话说,如果事件的因果链可以追溯到不以人工的角度评估的实体上。那么关于半机械人呢?由于它们的生物体中嵌入了一个或多个非生物部分,它们是否是人工的?无论有多少特例,A4都应该有助于评估在人工智能和合成生物学中什么是人工。此外,在A-Life等领域,断言“A-Life的方法和见解也在逐渐渗入生物学中,意味着计算建模现在在生物学的所有领域都很普遍。A-Life的成功是否意味着它被纳入对生命的主流研究中?[…]如果这种趋势继续下去,不久将来A-Life将不再是“人工””(Aguilar等人,2014:10)。我假设其他研究领域和科学领域很快也将不再以传统意义上的“人工”来看待。
在本文中,我认为由于新科学的出现和发展,即人工智能和合成生物学,传统的自然与人工之间的区别已经不再有用。人工智能和合成生物学主要以合成方法作为它们的建模方式,并以人造品或更广义地说为“人工实体”来实现。它们的构建标志着它们是人工的。尽管人工智能中的合成方法确实被使用,特别是在其发展的最初阶段,以推进与认知科学和心理生活研究(Cordeschi,2002)密切相关的“心理学”人工智能计划,但合成方法已经扩大到许多人工智能子领域,并具有不同的目标,这在机器人技术中最为明显。在合成生物学等其他学科中,合成方法被用来构建显示生物学中可能存在某种人工性质的人工生物实体,这可以改变其基本性质,并从理论、实验和伦理的角度进行考虑,而不仅仅是从工程的角度。人工智能朝向生物学的转变通过启发式的方式,是将人工性引入生物学的另一面,也改变了自然界。
我提议对“人工”的标准定义进行精细化,以达到一个更具体的新定义,能够对人工的新方面进行分类,这些新方面源于人工智能和合成生物学的发展,用于引领未来的科学研究朝着新的方向和新的机器发展。
Francesco Bianchini 是博洛尼亚大学科学哲学副教授,他对人工智能、认知科学和机器人学有着特别的研究兴趣。他的跨学科研究活动使他深入探索了科学学科之间的不同交叉点(从人工科学到生物学),以及这些学科与人文学科之间的交叉点,促进了不同学科领域之间在研究和学术教学观点上的相互影响。他还对一些形式的归纳推理特别感兴趣,尤其是类比和在科学解释中使用模型。
1 Both for Leibniz and for those who have discussed his ideas on it. To provide just one example of a pre- sent-day interpretation of Leibniz’s words about natural machines, according to Nachtomy they“are indi- visible units in the sense that they are defned and informed by a single rule of generation, compatible with their having an infnitely complex structure such as an infnite series or a fractal-like structure”(Nachtomy, 2011: 77).
2 See the Book II, chapter 8, of Aristotle’s Physics: «generally art in some cases completes what nature cannot bring to a fnish, and in others imitates nature. If, therefore, artifcial products are for the sake of an end, so clearly also are natural products.» (Aristotle, 1991: 32).
3 See the Book II, chapter 1, of Aristotle’s Physics.
4 For example, see Kätsyri et al. (2015) for a discussion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original hypothesis in the light of more recent empirical evidence.
5 The handbook has had four main editions in 1995, 2002, 2009, and 2020. This testifes for the fast evolu- tion of the discipline, and the necessity of a constant signifcant updating.
6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a perfect rationality and a bounded rationality is at the center of AI origins, at least as regards the human though simulation and modeling. See Simon (1957) for the beginning of the debate on rationality
7 Russell too provides an example of this trend by focusing on rationality (Russell, 1997) as well as he is an example of an author assuming we already know what an artifcial system is (Bringsjord, Govindarajulu, 2020).
8 On the synthetic method in AI and the need to choose the right constraints for modelling an AI system with an explanatory role see also Lieto (2021).
9 Both in a virtual and in a synthetic way, that is by computer simulation and building real artifacts respec- tively, according to a distinction made by Harnad (1994). As previously said, such a distinction is not clear- cut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the process of testing and validating a scientifc cognitive theory through the synthetic method.
10 See the conclusion of Mead (1990). On large-scale adaptive analog technology and Very-Large-Scale- Integration (VLSI) digital circuits see also Mahowald, & Douglas (1991).
11 On robotic modeling in cognitive science see Morse et al. (2011). On the“biological”difculty to scale the complexity of living beings to build robots at a human-cognition level in situated robotics see the wor- ries by Brooks dating back to 1997:“Perhaps it is the case that all the approaches to building intelligent systems are just completely of-base, and are doomed to fail. […] Perhaps we have all missed some organ- izing principle of biological systems, or some general truth about them. Perhaps there is a way of looking at biological systems which will illuminate an inherent necessity in some aspect of the interactions of their parts that is completely missing from our artifcial systems”(Brooks, 1997: 300–301, emphasis added).
12 Craig Venter, the head of the Research Institute that has created this minimal-genome organism, called it“Mycoplasma Laboratorium”or“Synthia”and the announcement of its creation is quite recent (Service, 2016).
13 For the issue of prediction in entities of synthetic biology see Bianchini (2018).
14 Today synthetic cells “are more machine-like (robot-like) than organism-like (“machine” here is intended in its classical meaning, i.e., a device that is built/programmed to perform certain operations decided by the machine builder)” (Stano, 2019: 1–2).
15 Interesting remarks on this subject are already in Hofstadter (1979), in a chapter about self-reference and self-replication and ending with a paragraph entitled“The Origin of Life”.
16 For an example in biology see Forber (2010).
17 For example, artifcial biological systems built on the base of expanded artifcial genetic alphabets (for one example, see Georgiadis (2015)). See also Warren (2019).
18 The tradition of describing AI as a history of good and bad period is not recent. See for example Crevier
19 See, for example, the Merriam-Webster English dictionary: https://www.merriam-webster.com/dicti onary/artifcial (last retrieval March 14th, 2021).
20 For a survey on this topic concerning many AI systems, from algorithms to robots, see Lawless et al. (2017).
Aguilar, W., Santamaría-Bonfl, G., Froese, T., & Gershenson, C. (2014).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of
artifcial life. Frontiers in Robotics and AI. https://doi.org/10.3389/frobt.2014.00008
Aristotle. (1991). Physics, from J. Barnes (ed.), The Complete works of Aristotle. The revised oxford transla-
tion, vol. 1.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Benner, S. A., Yang, Z., & Chen, F. (2011). Synthetic biology, tinkering biology, and artifcial biology.
What are we learning? Comptes Rendus Chimie, 14(4), 372–387.
Bensaude-Vincent, B. (2007). Reconfguring nature through syntheses: From plastics to biomimetics. In B. Bensaude-Vincent & W. R. Newman (Eds.), The artifcial and the natural. An evolving polarity (pp.
Bensaude-Vincent, B., & Newman, W. R. (2007). Introduction. The artifcial and the natural: State of the
problem. In B. Bensaude-Vincent & W.R. Newman (Eds.), The artifcial and the natural. An evolving
polarity (pp. 1– 19). MIT Press.
Bianchini, F. (2018). The problem of prediction in artifcial intelligence and synthetic biology. Complex
Boden, M. A. (2009). Computer models of creativity. AI Magazine, 30(3), 23–34. https://doi.org/10.1609/
Bringsjord, S., & Govindarajulu, N. S. (2020). Artifcial intelligence. In E. N. Zalta (Ed.), The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Summer 2020 Edition), https://plato.stanford.edu/archives/sum2020/entri
es/artifcial-intelligence/.
Brooke, J. H. (2007). Overtaking nature? The changing scope of organic chemistry in the nineteenth cen-
tury. In B. Bensaude-Vincent & W. R. Newman (Eds.), The artifcial and the natural. An evolving
polarity (pp. 275–292). MIT Press.
Brooks, R. A. (1997). From earwigs to humans. Robotics and Autonomous Systems, 20(2–4), 291–304.
https://doi.org/10.1016/S0921-8890(96)00064-4
Chemero, A. (2009). Radical embodied cognitive science. MIT Press.
Church, G. M., & Regis, E. (2012). Regenesis. Basic Books.
Cordeschi, R. (2002). The discovery of the artifcial. Mind and Machines Before and Beyond Cybernetics,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Cordeschi R. (2008). Steps toward the synthetic method: Symbolic information processing an sel-organizing
systems in early artifcial intelligence modeling. In P. Husband, O. Holland, & M. Wheeler (Eds.), The
mechanical mind in history (pp. 219–258). MIT Press.
Crevier, D. (1993). AI: The tumultuous search for artifcial intelligence. Basic Books.
Damiano, L., & Stano, P. (2018). Synthetic biology and artifcial intelligence: Grounding a cross-discipli-
nary approach to the synthetic exploration of (embodied) cognition. Complex Systems, 27(3), 199–228.
Datteri, E., & Tamburrini, G. (2007). Biorobotic experiments for the discovery of biological mechanisms.
Philosophy of Science, 74(3), 409–430. https://doi.org/10.1086/522095
Deplazes, A., & Huppenbauer, M. (2009). Synthetic organisms and living machines: Positioning the prod- ucts of synthetic biology at the borderline between living and non-living matter. System and Synthetic
Di Paolo, E. A., (2003). Organismically-inspired robotics: Homeostatic adaptation and natural teleology
beyond the closed sensorimotor loop. In K. Murase & T. Asakura (Eds.), Dynamical systems approach
to embodiment and sociality (pp. 19–42), Advanced Knowledge International.
Dumouchel, P., & Damiano, L. (2017) Living with robots. Harward University Press.
Floreano, D., & Mattiussi, C. (2008). Bio-inspired artifcial intelligence theories, methods, and technolo-
Forber, P. (2010). Confrmation and explaining how-possible. Studies in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Biologi-
cal and Biomedical Sciences, 41(1), 32–40. https://doi.org/10.1016/j.shpsc.2009.12.006
Georgiadis, M. M., Singh, I., Kellett, W. F., Hoshika, S., Benner, S. A., & Richards, N. G. J. (2015). Struc-
tural basis for a six nucleotide genetic alphabet.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 137(21),
6947–6955. https://doi.org/10.1021/jacs.5b03482
Hamad, S. (1994). Levels of functional equivalence in reverse bioengineering. Artifcial Life, 1(3), 293–301.
Hofstadter, D. R. (1979). Gödel. An Eternal Golden Braid. Basic Books.
Katrekar, D., Chen, G., Meluzzi, D., Ganesh, A., Worlikar, A., Shih, Y., Varghese, S., & Mali, P. (2019).
In vivo RNA editing of point mutations via RNA-guided adenosine deaminases. Nature Methods, 16,
239–242. https://doi.org/10.1038/s41592-019-0323-0
Kätsyri, J., Förger, K., Mäkäräinen, M., & Takala, T. (2015). A review of empirical evidence on diferent
uncanny valley hypotheses: Support for perceptual mismatch as one road to the valley of eeriness.
Frontiers of Psychology. https://doi.org/10.3389/fpsyg.2015.00390
Knuuttila, T., & Loettgers, A. (2013). Synthetic modeling and mechanistic account: Material recombination
and beyo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80, 874–885. https://doi.org/10.1086/673965
Koskinen, R. (2017). Synthetic biology and thesearch for alternative genetic systems: Taking how-possibly
models seriously. European Journal for Philosophy of Science, 7(3), 493–506. https://doi.org/10.1007/
Koskinen, R. (2019). Multiple realizability as a design heuristic in biological engineering. European Jour- nal for Philosophy of Science. https://doi.org/10.1007/s13194-018-0243-3
Lawless, W. F., Mittu, R., Sofge, D., & Russell, S. (2017). Autonomy and artifcial intelligence: A threat or
Lieto, A. (2021). Cognitive design for artifcial minds. Routledge.
Mahowald, M., & Douglas, R. (1991). A silicon neuron. Nature, 354, 515.
Mead, C. (1990). Neuromorphic electronic systems. Proceedings of the IEEE, 78(10), 1629– 1636. https://
Mori M. (1970). Bukimi no tani (The uncanny valley). Energy, 7(4), 33–35 (translated and reprinted by K.
F. MacDorman & N. Kageki in IEEE Robotics & Automation Magazine, 19(2), 98– 100. https://doi.
org/10.1109/MRA.2012.2192811).
Morse, A., Herrera, C., Clowes, R., Montebelli, A., & Ziemke, T. (2011). The role of robotic modeling in
cognitive science. New Ideas in Psychology, 29(3), 312–324. https://doi.org/10.1016/j.newideapsych.
Nachtomy, O. (2011). Leibniz on artifcial and natural machines: Or what it means to remain a machine to
the least of its parts. In J. E. H Smith & O. Nachtomy (Eds.), Machines of Nature and Corporeal Sub-
stances in Leibniz (pp. 61–80), Springer.
Poon, C., & Zhou, K. (2011). Neuromorphic silicon neurons and large-scale neural networks: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Frontiers in Neuroscience. https://doi.org/10.3389/fnins.2011.00108
Preston, C. J. (2018). The synthetic age. Outdesigning evolution, resurrecting species, and reengineering Our world. MIT Press.
Reardon, S. (2020). Step aside CRISPR, RNA editing is taking of. Nature, 578, 631–632.
Russell, S. (1997). Rationality and intelligence. Artifcial Intelligence, 94, 57–77.
Russell, S. J., Norvig, P. (2009). Artifcial intelligence: A Modern Approach. Pearson.
Service, & R. F . (2016). Synthetic microbe has fewest genes, but many mysteries. Science, 351(6280), 1380– 1381. https://doi.org/10.1126/science.351.6280.1380
Shoham, Y., & Leyton-Brown, K. (2009). Multiagent systems: Algorithmic, game-theoretic, and logical
foundatio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imon, H. A. (1957). Models of man. Wiley.
Sprinzak, D., & Elowitz, M. B. (2005). Reconstruction of genetic circuits. Nature, 438(7067), 442–448.
Stano, P. (2019). Is Research on “Synthetic Cells” moving to the next level? Life. https://doi.org/10.3390/
Turing, A. M. (1948). Intelligent machinery. Report to executive committee of the national physics labo- ratory. In D. C. Ince (Ed.), Collected works of A.M. turing: Mechanical intelligence (pp. 107– 127).
Turing, A. M. (1950). Computing machinery and intelligence. Mind, 59, 433–460, (reprinted in J. Copeland
(Ed.), The essential Turing (pp. 441–464),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Warren, M. (2019). Four new DNA letters double life’s alphabet. Nature, 566, 436. https://doi.org/10.1038/
Weisberg M. (2013). Simulation and similarity: Using models to understand the World. Oxford University
Wulfram, G., & Werner, K. M. (2002). Spiking neuron models: single neurons, populations, plasticit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Zhang, F., Wen, Y., & Guo, X. (2014). CRISPR/Cas9 for genome editing: Progress, implications and challenges. Human Molecular Genetics, 23(R1), R40–R46. https://doi.org/10.1093/hmg/ddu125Ziemke, T. (2016). The body of knowledge: On the role of the living body in grounding embodied cognition. Bio Systems, 148, 4– 11. https://doi.org/10.1016/j.biosystems.2016.08.005
大模型与生物医学:
AI + Science第二季读书会
生物医学是一个复杂且富有挑战性的领域,涉及到大量的数据处理、模式识别、理论模型建构和实验验证等问题。AI基础模型的引入,使得我们能够从前所未有的角度去观察和理解这个领域的问题,加速科学研究的步伐,提高医疗服务的效率和效果。这种交叉领域的合作,标志着我们正在向科技与生物医学深度融合的新时代迈进,对于推动科学研究、优化医疗服务、促进人类健康有着深远的影响。
集智俱乐部联合西湖大学助理教授吴泰霖、斯坦福大学计算机科学系博士后研究员王瀚宸、博士研究生黄柯鑫、黄倩,华盛顿大学博士研究生屠鑫明,共同发起以“大模型与生物医学”为主题的读书会,共学共研相关文献,探讨基础模型在生物医学等科学领域的应用、影响和展望。读书会已完结,现在报名可加入社群并解锁回放视频权限。
详情请见:
大模型与生物医学:AI + Science第二季读书会启动
人类大脑是一个由数以百亿计的神经元相互连接所构成的复杂系统,被认为是「已知宇宙中最复杂的物体」。本着促进来自神经科学、系统科学、信息科学、物理学、数学以及计算机科学等不同领域,对脑科学、类脑智能与计算、人工智能感兴趣的学术工作者的交流与合作,集智俱乐部联合国内外多所知名高校的专家学者发起神经、认知、智能系列读书会第三季——「计算神经科学」读书会,涵盖复杂神经动力学、神经元建模与计算、跨尺度神经动力学、计算神经科学与AI的融合四大模块,并希望探讨计算神经科学对类脑智能和人工智能的启发。读书会从2024年2月22日开始,每周四19:00-21:00进行,持续时间预计10-15周,欢迎感兴趣的朋友报名参与,深入梳理相关文献、激发跨学科的学术火花!
详情请见:计算神经科学读书会启动:从复杂神经动力学到类脑人工智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