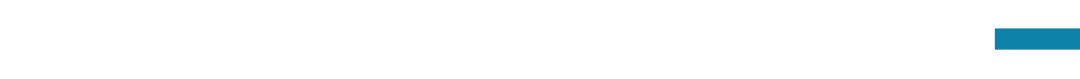2021年12月,PNAS 发布《政治极化动力学》(Dynamics of Political Polarization Special Feature)特刊,梳理了关于美国公共舆论两极分化现象的研究。特刊邀请复杂系统与计算社会学家 Scott E. Page 与纽约大学教授、长期从政治社会学与公共舆论研究的 Delia Baldassarri 对相关论文做了详细评述。Baldassarri 认为,意识形态与情感上的两极分化相结合,导致公众无法就事实达成一致;情感两极分化很可能导致失控,并威胁到当代民主的多元化基础。Page 从复杂自适应系统视角分析了不同模型,探讨了走出当前两极分化格局的道路。今天的文章是该评述文章的翻译。
研究领域:政治极化,复杂系统,群体动力学,反馈
Delia Baldassarria, Scott E. Page | 作者
李倩倩 | 译者
王玉龙 | 审校
邓一雪 | 编辑
文章题目:
The emergence and perils of polarization
https://www.pnas.org/content/118/50/e2116863118
我们为《政治极化动力学》特刊中的论文提供了一些评议。Baldassarri 从理论上区分了意识形态党派(ideological partisanship)和情感党派(affective partisanship),她认为前者一般植根于社会人口和政治分歧,而情感党派则主要受情感依恋和排斥心理影响,而非意识形态和物质利益推动。她认为,后者很可能导致失控,并威胁到当代民主的多元化基础。Page认为,综述许多不同模型的贡献可能比单独论述某一个模型的贡献更大。特刊中的每篇论文都指出了两极分化的不同原因以及潜在的解决方案。总体来看,这些论文表明,造成两极分化的多种原因可能会自我强化,这表明成功的干预需要大量努力。而要理解如何构建这样的干预措施可能需要更大的现实模型。
Baldassarri:情感两极分化的危险:当党派身份战胜社会分裂
受民主政治理论的启发,学者们广泛研究了(美国和其他国家)公众舆论的两极分化,寻找意识形态和问题维度上极端主义增加的迹象,以及沿着多重社会分裂的利益结盟/整合[1, 2]。根据衡量意识形态两极分化的标准,美国公众舆论并没有真正变得更加分裂。相反,美国公民在很大程度上被分为党派阵营:在民主党和共和党中,我们观察到政治观点和政党认同之间有更大的一致性,尽管总体公众在大多数政治问题上并没有变得更加极端[3, 4]。然而,根据一些人的说法,这种党派分类已经对政治结构产生了可怕的后果。两个政党在意识形态上都变得更加同质化[5],彼此泾渭分明,其支持者的形象也变得几乎定型。
与几十年前相比,如今的政治标签——民主党、共和党、保守党、自由党——在群体内的认同方面,特别是在群体外的敌意方面,都引起了强烈的情感反应。情感两极分化影响着政治观点的形成,既包括像新冠肺炎这样的新问题,又包括对社会生活不同方面的既定偏好和实际行为,如愿意与支持不同政党的人交谈、约会和生活在一起[6],并延伸到通常被认为与政治无关的生活领域,例如是否需要戴口罩或接种疫苗等与健康相关的决定[7]。
一些人认为,这种新形式的党派认同主要是由情感依恋/排斥,而不是政治意识形态和物质利益推动的[8, 9],尽管其他人反而指出了党派仇恨的政策性质 [10] ,或者认为,党派身份和政策分歧都可能影响人际交往[11]。在这篇评议中,我首先解释一种植根于政治分裂和物质利益的党派认同形式与由群体情感依附动力学驱动下的党派认同之间的区别,在后者中,党派认同本身比社会人口背景和相关的物质和象征利益更为重要。无论是从意识形态的一致性还是从社交网络的动态性来看,党派认同是建立在社会经济特征和相关社会认同(如阶级、种族、性别、宗教、性)之上并受其制约,或者它本身成为一种动员性身份,能够压倒其他对立的身份和利益,这都是不同的。然后,我将根据这种分析性的区分来阅读本期特刊中的文章,并利用它们的见解来理解情感极化如何可能成为一个自我维持的失控过程,以及确定可能遏制它的方面。
社会分裂 vs. 党派认同。考虑到意识形态的两极分化,美国各党派和候选人在一大批政治问题上的分歧越来越大,包括经济、民权和道德问题,从而使其问题立场更加鲜明。一些人认为,这使得选民更容易认同任何一个政党的政治议程,并在政党之间进行分类。然而,政党在不同问题维度上的一致性使得具有特定社会人口学特征的群体难以定义他们的政治忠诚度,例如,一个富有的世俗人士是认同共和党的经济观点,还是认同民主党的道德观点?
事实上,研究表明,几乎没有证据表明公众在不同问题领域的意见一致(统一)[12],尽管这种现象在近年有所增加,特别是在参与政治的公民中[13]。如果考虑到政治信仰体系的异质性,研究结果甚至更具争议性:虽然三分之一的美国公民在组织他们的政治观点时符合意识形态的主流,但另外三分之一的人要么是经济上的自由主义者,要么是道德上的保守主义者,或者相反,从而表现出一种不同于政党提供的偏好组合[14]。然而,这种明显的不一致很容易用他们的社会人口特征和社会身份来解释,这支持了广泛的政治理论假设,即选民的态度和政策偏好与既定的社会经济裂痕相一致。只要潜在的社会分裂(如种族、阶级、宗教、性)是贯穿各领域的,增加社会分裂的维度就应该有助于融合。事实上,正是潜在冲突的整合(又称统一)被认为是对社会和政治凝聚力的威胁[15, 16]。
虽然意识形态的两极分化似乎受到个人在复杂社会中经历的利益、身份和社会网络的多重制约,但情感两极分化的本质及其与社会生活其他领域的关系并不那么明显。与美国过去的党派之争不同,当前的党派认同浪潮似乎在很大程度上以群体依恋动力学为特征,包括群体内认同和明显的群体外敌意。目前还不清楚共和党和民主党的党派身份在多大程度上超越了社会人口身份和相关的物质和象征利益,但有零散的证据表明,党派关系已经开始推动政治态度的形成,并为政治行为以及社会生活其他领域的行为提供信息,包括在哪里生活以及迄今为止与谁交往。“随着对政党的关注越来越多,这将导致按照政党路线对群体身份进行分类”[17]。
这是我们理解极化动力学的一个重要方面,它直接影响到任何试图对意识形态和关系动力学进行建模的尝试。例如,大多数意见变化和极化的正式模型都包含一定程度的党派同质化:平均而言,民主党人倾向于更频繁地与其他民主党人互动,而共和党人则更频繁地与其他共和党人互动。然而,这种模式是否是社会人口统计维度(如阶级、种族、宗教信仰、年龄、性别等与党派偏见相关、但并不一致的因素)上的同质性的副产品,或者相反,关系的模式很大程度上由政治党派偏见驱动。在第一种情况下,社会人口同质性不太可能带来完全的政治孤立——大多数人同时具有多重相互冲突的身份,例如,富有的、无宗教信仰的城市居民,道德上保守的少数族裔,或者受过教育的家庭主妇,从而接触一些不同政治观点。相反,如果政治党派在交往模式中占据主导地位,那么党派的同质性就不可避免了。即使是那些宁愿在异质性的基础上来选择他们的伴侣、朋友和熟人的人,也将不得不适应这样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们在生活的各个领域都穿着红色或蓝色的政治衬衫。
综上所述,这些考虑对极化动力学的发展有严重影响,包括两极分化是否可能成为一个自我维持的失控过程,或者更好地理解为一种短暂的表现,一种可能像它出现时那样突然结束的爆发。植根于社会人口学特征和政治裂痕的党派认同通常会限制政治两极化,只要有足够多的选民具有交叉性的身份,不会使他们太容易与任何一方结盟。相反,情感化的党派身份可能会引发一个失控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个人变得越来越两极化。他们的社会人口特征和兴趣的复杂性对总体的党派身份来说是次要的,而群体认同和自我选择进入政治同质化的社交网络的过程可能会无限期地持续。然而,关于在没有强有力的、连贯的政治叙事的情况下维持政治身份和党派间敌意的可能性,问题依然存在。这期特刊中的文章大大有助于巩固和扩大我们对这些动力学的理解,包括触发以及可能遏制两极分化的因素。
Stewart等人[17]建立了群体极化和政党分类的共同演化模型,假设与群体外个体的经济互动风险较大,而不利的经济条件则会增加风险厌恶。正如预期的那样,群体和政党身份的一致会降低群体外互动的可能性,从而导致更大的极化。若将两极分化与不断增长的经济不平等结合起来,会导致一个失控的过程。相比之下,当群体和政党身份没有强烈的一致性时,两极分化的风险就会降低。重要的是,通过提供公共物品、高水平的财富再分配可以缓解两极分化。
Kawakatsu等人[18]支持Madison和Blau的直觉,即增加议题的数量,以及减少每个人关心的议题的数量,都具有减少政治极化的效果。同时,通过博弈论模型,他们强调了在强大的党派认同下,群体内部合作和社会融合之间的内在张力。也就是说,党派偏见通过党派分类减少了问题的维度,这导致了更大的配对合作可能,但也导致了社会极化。值得注意的是,在Kawakatsu等人[18]的工作中,党派偏见的实现方式抓住了党派认同的首要机制。当政治偏见最大时,人们只会模仿自己党内的人的问题偏好。排除跨党派影响的可能性后,党内结盟增加,事实上将问题空间的维度降低为单一的党派维度。
同样,Axelrod等人[19]假设情感上的两极分化会降低对反对者的容忍度,并表明低水平的容忍度如何不可避免地导致温和多数的侵蚀,从而导致两极分化。虽然少数意识形态的极端分子可能会有加强温和多数的存在的效果,但太多的极端分子会把温和派推向极端。将这一发现与当前的美国环境联系起来,尽管情感极化尚未导致意识形态极端主义的增加,但这可能是下一步的预期。从与不同的人互动可能导致负面结果的假设出发,作者证明了多样性(与不同的人互动的可能性)可能导致更大的分裂。然而,与Baldassarri和Bearman[20]以及Szymanski等人[21]的研究结果相呼应,增加政治空间的维度可能会减少两极分化。如果在一个维度上出现了分类,它就会阻止其他维度上的极化。最后,引入对自我利益的考虑(并假设这是正态分布的,许多人倾向于温和的政策立场),对遏制两极分化具有宝贵的效果。
综合来看,这些贡献拓宽了我们对意识形态极化、问题维度和党派敌意之间互动的理解。它们还强调了在什么条件下将政治意识形态与经济利益挂钩可以防止极端的两极分化[17]。最后,他们明确指出,为了捕捉这些过程的非线性,需要采取复杂的系统方法。例如,Szymanski等人[21]和Leonard等人[22]都强调了临界点和自我强化动力学的存在,这导致了阶段性变化,使极化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
其他贡献通过考虑一系列背景因素补充了这一情况,包括党派媒体的作用、假新闻的性质、地理(错误)表示、空间隔离和排序。首先考虑信息环境,在线媒体和社交网络的兴起促进了内容和人际交往的个性化、新影响者的出现以及错误信息的传播。
Santos等人[23]考虑了匹配算法在同质在线社交网络中影响个体排序的作用。匹配算法通常倾向于优先与结构相似的节点建立联系,这可能会加强在线排序,并且鉴于在线社交网络在意见和信息传播中的作用,这可能会加剧观点极化。同样,Tokita等人[24]展示了社交网络是如何被极化的媒体生态系统和信息级联所重塑的:在一个意识形态极化的信息环境中,人们失去了跨领域的联系,将自己归类到同质的社交网络中。
不仅是在线媒体,物理隔离和外部冲击也可能通过突出某些政治问题来加剧大规模极化。例如,Chu等人[25]记录了反对乌克兰政府决定停止欧盟一体化进程的抗议浪潮如何产生了增加地理极化的效果。
特别是,当地的环境既影响了意见的变化,也影响了社交网络的重新洗牌。放大到关系动力学,Vasconcelos等人[26]展示了网络隔离如何阻碍合作。总的来说,一些文献认为,党派分歧倾向于抑制公共产品的全球供应链系统。事实上,国家舆论和政治利益相关者的两极化使得改革政策和国际条约更难通过[27]。
最后,正如Wang等人[28]所言,一系列的制度和其他因素都有助于改变政治代表性。当中间选民不是关键选民时,党内程序就会选出更极端的政治家。为了纠正美国民主的这种扭曲,作者主张进行制度上的修正,如排序选择投票和竞选资金、以及重新划分选区的改革。
结论。尽管我们大多数人都生活在政治泡沫中,但如果让我们想一想我们实际上认识的少数反对党成员,我们很可能会提供一个偏离民主党人与共和党人刻板印象的描述,例如,“我的表妹是共和党人,但她嫁给了一个少数族裔,是环保事业的志愿者”或“我的朋友是民主党人,但他去教堂,不喜欢同性恋。”事实上,大多数人并不符合共和党人或民主党人的刻板形象,因为这些确实是刻板的观点,并没有反映我们所居住的这个世界的复杂性。然而,当人们抽象地与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联系起来时,这种细微差别就消失了,例如,在回答气候变暖问题、政治投票或决定住在哪里时。正如这个特刊中的许多论文所表明的,社会分裂和党派认同之间的相互作用是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可以导致非常不同的平衡。当然,当政党身份在决定政治观点和社会互动模式方面凌驾于个人特质之上时,政治两极分化就会随之而来。
总的来说,当人们对于政治开始袖手旁观时,这不是民主的好兆头。为了发挥作用,政治多元化通常假定个人及其关系模式决定了他们的政治忠诚度。党派政治应保持在后台,组织利益和身份,但它不会支配日常生活和社会关系。相反,当政治身份和党派意识占据主导地位,并对人们选择的社会网络、采用的身份以及在公共场合表达的偏好产生实质性影响时,党派两极分化可能会成为一个失控的过程。现在理解当前情感两极分化的浪潮是否会永久性地重塑美国的政治和社会格局还为时过早,或者相反,它只是一种短暂的表现、一种迷恋,可能很快就会消退,可能会被其他类似的短暂而强烈的认同所取代。本期特刊中的文章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关于注意事项的见解。
日益加剧的两极分化将美国社会从一个重叠的利益共同体转变为两个互不相干的部落,这给我们的政治机构带来了压力,以至于建立共识似乎完全不可能。政策制定者难以妥协,在国内造成严重破坏,使国际协议难以谈判或维持 [27]。在人际层面,两极分化已经变得如此明显,以至于在学校、工作场所、志愿者组织和社会聚会中的互动,已经从建立共同的目标感和认同感,变得同样可能扩大不和谐。
正如这些文章所显示的,两极分化可以沿着两个轴线来衡量:一个是意识形态——对世界如何运作和政策的信念;一个是情感——不信任、不喜欢,以及意识形态群体之间缺乏社会联系。从这些论文中可以看出,这些极化并不是由一系列可逆的叠加效应造成的。相反,每一种类型的极化都通过反馈作用加强了另一种极化[19, 21, 22]。因此,标准的线性或收益递减的直觉并不适用;任何一系列的小干预都不可能改变我们的方向。
理解极化的粘性需要理解反馈。正反馈意味着小的影响可以累积成大的变化[29],负反馈使一个系统能够吸收大的冲击或干预。正如这些论文所解释的,两极分化是通过正反馈产生的:分歧会促进分歧。负反馈扼杀了在群体间建立桥梁的尝试,从而使它保持原状。
这一简单的描述为了解这组论文的逻辑提供了一个窗口。每篇论文都提供了通过积极和消极反馈产生和支持两极分化的机制,并且就如何摆脱困境提出了不同的政策建议。所有这些都表明通往一个更加宽容的社会的道路可能是漫长而崎岖的;我们可能会在一段时间内保持分裂 [21]。
这本令人印象深刻的论文集中的每篇论文都提供了强大的洞察力和直觉。参与这套论文集,使读者对起作用的竞争性和互补性社会力量有了细微的了解。如果说我有什么批评的话,那就是这本论文集缺乏一个包括多种力量的高粒度模型,该模型以政策评估的明确目标为目标,瞄准现实;[30],这一遗漏限制了我们制定全面行动方案的能力。
所有的论文都把情感极化的上升作为一个既定事实,这在政治家投票行为的双峰分布以及个人在物理世界和信息圈的聚集中都有体现。一般来说,无论是对税率的偏好还是移民政策,任何事情如果呈现双峰分布,表明一些奇怪的事情正在发生。产生双峰分布的一种方法是假设有两种力量:一种将人们聚集在一起,另一种将他们分开。从意识形态的均匀或正态分布开始(暂时忽略我们是如何开始的),并假设人们变得更像那些靠近他们的人,而远离那些离他们远的人[19]。毫不奇怪,这些假设产生了两极分化。不太明显的是,它们产生两个峰,而不是三个峰,从一个峰到两个峰的转变发生在一瞬间(临界点),并且一旦处于极化状态,改善群体之间互动的善意尝试可能会增加而不是减少极化,因为它鼓励人们分离。
第二种类型的模型依赖于网络产生双峰模式[21,25]。这些模型解释说,两极分化的部分原因是由于技术的变化使相似的人能够联系起来,并远离那些与我们意见不同的人。由此产生的网络由两个群体组成,群组间的联系只占很小的比例。与直觉相反的是,想要与那些与我们不同的人保持距离,与其说是一种两极分化的力量,不如说是那些像我们这样的人——我们自我组装的回音室——所带来的吸引力[23]。
两极分化的网络限制了我们的信息,降低了对不确定环境下信息的信任度。虽然两极分化的网络并不排除在真相上的趋同或妥协,但它们会使趋同的速度慢到超出任何实际的时间尺度[31]。
这前两类模型都是依靠同质性与相似性来产生极化。第三种类型的模型将两极分化解释为对现代世界日益增长的维度的回应。过去,政策辩论只在几个方面进行:公平与效率或短期与长期,而目前的政策必须考虑到无数的影响。联合国推动了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每个目标又分为大约10个具体目标,每个具体目标都有几个经验指标。公民不可能监测所有这些变量,他不可能控制所有变量,也不可能(或的确可能)关心所有变量。
James Madison认为,议题的多样性是有益的,因为它可以通过产生交叉性分歧来防止两极分化:每个议题都会产生不同的支持者联盟[18]。当利益群体在问题上存在分歧时,我们会遇到前面提到的混乱,每个人都会同意或者不同意其他人,但我们可能相处融洽,我们不会分裂成两个互不关联的意识形态部落。相反,我们每个人都在社会的各个层面上建立了一定程度的信任和相互尊重。
Madison没能预见到选举和媒体的激励措施会如何利用现代世界的压倒性维度,将我们引入至意识形态集群。其逻辑是这样的,由于无法逐一决定问题,公民希望精英和政治领袖能够简化——告诉我们如何思考。政党领袖、收视率驱动的媒体和社会影响者有动机建立忠诚的、意识形态上聚集的支持者网络。因此,我们得到的不是重叠派系的多样性,而是有害的维度缩减,其中每个公民、政治家和提案都选择全红或全蓝[18]。
正如这些论文所表明的,正是意识形态和情感上的两极分化的结合证明了这一点。意识形态两极分化(并没有增加多少)本身并不一定会破坏我们的体制。我们可能对依靠公共部门还是私营部门来减少贫困持有不同的想法,但仍能和睦相处,并期望我们的正式和非正式机构能在妥协的基础上制定明智的政策。但是,当与情感上的两极分化配对时,意识形态上的两极分化会导致我们无法就事实达成一致(或假装无法达成一致),我们就会越过那条在国家广场上游行和冲进国会大厦的分界线。
在我们这个情感两极分化的社会中,我们做出决定并采取行动,以加强我们自己集群内的联系。由于上述原因,这些集群在意识形态上变得越来越同质化。当我们停止与其他群体互动时,我们就失去了在一个整合的、多元化的社会中会产生的经济和社会利益[17]。就像保守派人士不会从左翼面包师那里买生日蛋糕、自由主义者不会加入右翼银行家的匹克球联盟。因此,我们缺乏获取各种知识的途径,而这些知识可能会提高我们在生活的其他方面做出正确决定的能力[24]。
那么,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我们怎样才能摆脱目前的处境呢?首先,我们必须意识到为什么我们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必须采取实质行动,要直观地解释其中的原因,可以考虑一个有两个总变量的模型:一个代表意识形态两极分化的程度,另一个代表情感两极分化的程度,两者之间的反馈既有可能稳定,也有可能是两极分化的。假设这样一个系统产生了两种平衡:一种是宽容的,另一种是极化的。在宽容的平衡中,我们信任、倾听并相处,我们在问题上达成共识。此外,我们较低的意识形态两极分化建立了信任。
在情感和意识形态两极分化的平衡中,我们限制了我们的政治和社会机构的功能 [22]。我们与其他群体的共识越少,我们的互动就越少,而我们互动越少,我们就越不信任,越不相信他们所说的话。我们的回声室仍然根深蒂固。
这些平衡中的每一个都有吸引盆地(basins):把系统推到平衡吸引盆地中的任何一点,系统都会马上回到平衡状态。考虑一个只有一个变量——即容忍度的模型。处于极化平衡的社会只有在一系列冲击使容忍度超过阈值,即临界点的情况下,才能逃脱并进入容忍的平衡。如果容忍度的提高没有超过临界点,就会导致两极化平衡的重新出现。换句话说,为减少意识形态和情感上的两极分化而做出的用心良苦的努力,如果仍然处于两极分化平衡的吸引盆地中,就不会有长期的效果。
正如本论文集中的几篇论文所示,极化平衡的盆地的大小取决于自我强化过程的数量和强度。在最好的情况下,产生容忍度的阈值与退出它所需的阈值相同。然而,如果存在多种力量在起作用,要退出高度极化状态,容忍度可能必须超过导致社会进入极化状态的阈值。换句话说,这个系统可能有一个很厚的边界:走出极化状态可能需要比进入极化状态付出更多努力。这是真的,原因类似于为什么减掉10磅体重比增加10磅更难:我们的身体通过自我强化的反馈来抵制减重,一旦我们体重增加,我们就会增加需要食物的细胞。
在政治领域,边界可以变得如此之厚,以至于几乎不可能逃脱一种平衡。根据一篇论文[21]所说,在某些条件下,一个系统会表现出不可逆性。可以说,即使我们可以将容忍度提高到比如说11,也无法逃脱极化平衡。
理想的情况是,我们的政治体系不会两极分化,而是处于一个宽容的平衡状态,有一个大的吸引盆地,这样,在政治体系的正常冲击下,加剧两极分化的冲击会被吸收,宽容会被重新建立。但不幸的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要想摆脱两极分化的状态,需要了解我们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而且,如前所述,这些论文提供了两极分化的不同原因。与其把这些论文提供的独特见解视为相互竞争,不如将每篇论文都视为一个复杂过程中特定维度的亮点[32]。当然,这些论文涵盖的所有力量在某种程度上都在起作用,而且它们很可能相互加强。当我们拉开距离时,我们与志同道合的人形成网络时,他们更有可能接受方便的、未受质疑的、简单的框架。
这些不同影响的相互依存性表明了一个更细化模型的潜在价值,它包括更多类型的个人,以及像社区组织这样的中间层次结构。在大多数情况下,本特刊中相对呆板的模型将两极分化描述为一种稳定的平衡状态。在这样做的时候,他们忽略了政治、经济和社会系统的复杂性。相比之下,更细粒度的基于主体的模型中,个人适应信息和事件,将我们的两极分化的社会概念转化为一种具有生命的社会,不断回应和吸收新的行为者和想法。这些适应意味着一连串不断变化的联系、信仰、行为和规范,而不一定是平衡的。
在复杂的系统模型中,稳定平衡的概念被稳健配置的概念所取代:为保持核心功能而适应的特征或属性的集合。政策变化产生了系统的反应,个人调整他们的意识形态,改变他们的网络,甚至可能转换忠诚度。在一个联邦系统内,州一级的政治家可能会尝试政策,以维持他们的支持度。而配置永远在变化,如果这个系统是强大的,那么它就会保留关键的特征和组成部分[33]。
为了看到平衡和复杂性观点之间的区别,考虑一下国会大厦被攻陷事件的影响。虽然这是一个重大事件,但它并没有让我们摆脱两极分化的状态,它也不是没有任何影响。我们现在发现自己处于非常不同的情况:组成员身份已更改,一些人脱离了共和党,其他人却变得更加忠诚。因此,我们的两极分化不应该被视为是固定的,而是处于不断变化之中。
我无意贬低从平衡模型中得出的见解。恰恰相反:这些模型产生了大量的思想食粮,并提供了构建更细粒度的复杂系统模型的基础。
为了找到一条走出当前两极分化格局的道路,可能需要一系列更精细的模型——根据种族、地点、收入和意识形态对人们进行分类的模型。因为正如本文所展示的,我们的两极分化有多种原因。因此,有理由认为,提高容忍度的有效政策需要多管齐下的干预。其中一些是自上而下的:减少不公正的选区划分,通过排序选择投票消除单一成员选区[34],以及从社交媒体上删除传播虚假信息的人和机器人。其他的,比如跨团队建立有意义的、持续的互动,这是自下而上的。
高保真模型——那些包括多个原因和多个社区的模型,这些模型提供了探索政策如何相互作用的可能性。哪些是互补的,哪些是可替代的?换句话说,一加一什么时候等于三,什么时候又等于一?在我们的各种利益、政治信仰、经济框架和文化身份相互交叉和重叠的山上建设一个光辉的城市,以创造一个充满活力、创新、可持续和宽容的社会,这需要对如何构建自我强化的干预措施有细致入微的了解。
总之,这些论文成功地确定了两极分化的诸多原因,揭示了其逆转的复杂性,并描述了一系列潜在工具的特点。一组更大的模型将它们结合在一起,可以帮助我们确定哪一组政策可能配合得最好,以及应用它们的顺序和规模。
凭借其特有的敏锐分析能力,Page深入探讨了这期特刊中提出的各种政治极化模式的本质,并确定了它们所基于的各种构建模块。从复杂适应系统的角度来看,下一步是一个全面的方法,即“高粒度模型……以现实主义为目标”帮助我们理解不同的因素是如何共同作用的。在我看来,第一个挑战在于对每一个动态的功能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做出合理的假设,并对模型进行经验性的校准。
由于现有的实证研究没有提供足够可靠的核心信息,因此这一点变得很困难,包括 1)在何种条件下与持有不同政治观点和/或属于反对党的人接触会增加或减少社会分裂;2)精英、意见领袖和大众极化之间的反馈程度,以及各自的驱动因素是什么;3)政治空间的维度(模型显示它很重要,但不清楚我们是否应该根据政治问题、社会分裂或社会人口结构断裂来建立维度模型);以及4)对社交网络和信息环境的分类在多大程度上是由党派身份所驱动的,或者相反,是源于日常生活经历,而这些经历在本质上不一定是政治性的。
第二个挑战包括在全面性和简明性之间取得适当的平衡。例如,Page在他的评论中指出了三种可能产生双峰模式的方式(吸引-排斥、社交网络和问题的多重性)。我们的模型应该以哪一种为基础?还是应该把它们都纳入模型?回答这些问题需要接受一个具体的理论,即大众极化的原因是什么,以及先验地确定哪些反馈回路是相关的,哪些可以被忽略。类似地,我们应该考虑几代人之间的意识形态变化吗?30年前自我认同的共和党人(或民主党人)在政治观点和一些社会人口统计数据方面与今天的共和党人截然不同,这对以现实主义为目标的多层次模型有影响吗?
当我们思考政治极化的细化模型应该包括什么时,这些只是我们能想到的少数。矛盾的是,如果我们完全确定地知道所有这些事情,我们可能不需要这个模型。然后,我们的最佳行动方案变成在多种基础上向前推进,让形式化的模型和实证研究相互支持。
Baldassarri强调了这样一个世界的可怕后果,在这个世界里,我们的政治意识形态在我们如何建立社会关系方面发挥着主导作用。如果政党决定政策议程,并强迫我们在大多数政策的两个极端解决方案之间做出选择,而不是对多元化社会产生的利益和关切做出反应,美国将成为一个不太理想的居住地。我们的社会互动将经常是有争议的。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将被意识形态所歪曲。而我们应对减少不平等、实现可持续增长和应对疫情危机的能力也将受到限制。
她的视角可以拓宽以考虑其他社会变化可能会间接放大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首先,考虑当前新冠大流行期间的掩蔽和疫苗接种选择。这些都与政治意识形态密切相关,尽管并不完美,但共和党人不太可能推动这两种观点中的任何一种。
与可以掩盖的,如为有孩子的家庭提供收入补贴的立场不同,是否戴口罩的立场在家庭、组织或社交网络中是无法避免的。我们可以选择不谈论阿富汗,甚至不谈论我们是否支持堕胎。我们无法回避关于口罩和疫苗的决定;一个人不戴口罩或接种疫苗会让其他人付出代价。
比如说,在一个家庭或组织内部,我们面临着一个由来已久的选择,是退出还是发声?如果我们是反对戴口罩群体的一员,我们可以选择退出,或者我们可以行使我们的声音。我们在多大程度上这样做取决于我们对相关群体的忠诚度[35]。随着我们对红色或蓝色意识形态集团的从属关系变得更加突出,这是否会降低我们对其他团体的忠诚度?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影响可能会更加可怕。
再想想我们工作场所中日益严重的种族隔离现象。学术界越来越倾向于左派,尤其是在文科系和教职员工中。牧场主、伐木工、牙医和外科医生则更加右倾。而且,基于这些论文,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按工作分类导致的分化只会增加。左翼的柑橘种植者和右翼的当地书商可能会成为公共广播电台和互联网点击网站的素材。
撇开玩笑不谈,海军陆战队已经成为坚实的右翼,而我们的精神病医生几乎完全是左翼,这一事实应该引起关注。我们不仅可能不想召集海军陆战队来防止右翼集团的阴谋,我们也可能不想让精神病医生来决定是否应该用市场来分配一些药物。意识形态的多样性不仅在政治领域,而且在几乎所有领域都是制定良好决策的必要条件。
让事情变得更复杂的是,在党派身份仍然混合在一起的工作场所——银行、保险、批发、销售、个人服务、医疗支持人员、商业运营以及(是的)经济学家——在家工作的能力意味着这些领域的人们可能不需要像过去那样克服差异。
极化甚至可能对核心问题施加压力。在2014年,一个潜在的伙侣是否与你一样相信通过总量管制和排放交易政策来解决污染问题的市场解决方案,可能不会成为关系的破坏因素,但他是否戴口罩并相信2020年的总统选举结果,如今可能会。就政治认同进入我们对生活伴侣的选择而言,消除两极分化变得更具挑战性。
最后,从更积极的角度来看,两极分化最终可能会导致自身的毁灭。正如Baldassarri在她的文章中提到的,意识形态的两极分化并没有增加那么多。如果我们中有足够多的人渴望一个更宽容的社会,我们可以行动起来,我们可以在不同群体之间搭建桥梁,减少两极分化。与其他群体的互动,尽管看起来很困难,但如果我们以谦逊的态度行事,就会变得更容易:如果我们认识到,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对我们面前的复杂挑战和机遇拥有所有的答案,我们都可以通过花时间和努力倾听他人的想法而受益。
1 P. DiMaggio, J. Evans, B. Bryson, Have American’ s social attitudes become more polarized? Am. J. Sociol. 102, 690–755 (1996).
2 M. P. Fiorina, S. J. Abrams, Political polarization in the American public. Annu. Rev. Polit. Sci. 11, 563–588 (2008).
3 M. Levendusky, The Partisan Sort: How Liberals Became Democrats and Conservatives Became Republican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9).
4 D. Baldassarri, A. Gelman, Partisans without constraint: Political polarization and trends in American public opinion. AJS 114, 408–446 (2008).
5 S. W. Webster, A. I. Abramowitz, The ideological foundations of affective polarization in the U.S. electorate. Am. Polit. Res. 45, 621–647 (2017).
6 S. Iyengar, Y. Lelkes, M. Levendusky, N. Malhotra, S. J. Westwood, The origins and consequences of affective polariz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nnu. Rev.
Polit. Sci. 22, 129–146 (2019).
7 J. N. Druckman, S. Klar, Y. Krupnikov, M. Levendusky, J. B. Ryan, Affective polarization, local contexts and public opinion in America. Nat. Hum. Behav. 5,
8 S. Iyengar, G. Sood, Y. Lelkes, Affect, not ideology: A social identity perspective on polarization. Public Opin. Q. 76, 405–431 (2012).
9 L. Mason, Uncivil Agreement. How Politics Became Our Identit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8).
10 L. V. Orr, G. A. Huber, The policy basis of measured partisan animos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Am. J. Pol. Sci. 64, 569–586 (2020).
11 N. Dias, Y. Lelkes, The nature of affective polarization: Disentangling policy disagreement from partisan identity. Am. J. Pol. Sci., 10.1111/ajps.12628 (2021).
12 B. Park, How are we apart?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the structure of ideological disagreement in the American public, 1980–2012. Soc. Forces 96, 1757–1784
13 A. C. Kozlowski, J. P. Murphy, Issue alignment and partisanship in the American public: Revisiting the ‘partisans without constraint’ thesis. Soc. Sci. Res. 94,
14 D. Baldassarri, A. Goldberg, Neither ideologues nor agnostics: Alternative voters’ belief system in an age of partisan politics. AJS 120, 45–95 (2014).
15 P. Blau, Parameters of social structure. Am. Sociol. Rev. 39, 615–635 (1974).
16 D. Baldassarri, M. Abascal, Diversity and prosocial behavior. Science 369, 1183–1187 (2020).
17 A. J. Stewart, J. B. Plotkin, N. McCarty, Inequality, identity, and partisanship: How redistribution can stem the tide of mass polarization. Proc. Natl. Acad. Sci.
U.S.A. 118, e2102140118 (2021).
18 M. Kawakatsu, Y. Lelkes, S. A. Levin, C. E. T arnita, Interindividual cooperation mediated by partisanship complicates Madison’ s cure for “mischiefs of faction.” Proc. Natl. Acad. Sci. U.S.A. 118, e2102148118 (2021).
19 R. Axelrod, J. J. Daymude, S. Forrest, Preventing extreme polarization of political attitudes. Proc. Natl. Acad. Sci. U.S.A. 118, e2102139118 (2021).
20 D. Baldassarri, P. Bearman, Dynamics of political polarization. Am. Soc. Rev., 72, 784–811 (2007).
21 M. W. Macy, M. Ma, D. R. T abin, J. Gao, B. K. Szymanski, Polarization and tipping points. Proc. Natl. Acad. Sci. U.S.A. 118, e2102144118 (2021).
22 N. E. Leonard, K. Lipsitz, A. Bizyaeva, A. Franci, Y. Lelkes, The nonlinear feedback dynamics of asymmetric political polarization. Proc. Natl. Acad. Sci. U.S.A.
23 F. P. Santos, Y. Lelkes, S. A. Levin, Link recommendation algorithms and dynamics of polarization in online social networks. Proc. Natl. Acad. Sci. U.S.A. 118, e2102141118 (2021).
24 C. K. T okita, A. M. Guess, C. E. T arnita, Polarized information ecosystems can reorganize social networks via information cascades. Proc. Natl. Acad. Sci. U.S.A.118, e2102147118 (2021).
25 O. J. Chu, J. F. Donges, G. B. Robertson, G. Pop-Eleches, The microdynamics of spatial polarization: A model and an application to survey data from Ukraine.Proc. Natl. Acad. Sci. U.S.A. 118, e2104194118 (2021).
26 V. V. Vasconcelos et al., Segregation and clustering of preferences erode socially beneficial coordination. Proc. Natl. Acad. Sci. U.S.A. 118, e2102153118 (2021).
27 C. Perrings, M. Hechter, R. Mamada, National polar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 agreements. Proc. Natl. Acad. Sci. U.S.A. 118, e2102145118 (2021).
28 S. S.-H. Wang, J. Cervas, B. Grofman, K. Lipsitz, A systems framework for remedying dysfunction in US democracy. Proc. Natl. Acad. Sci. U.S.A. 118, e2102154118 (2021).
29 S. E. Page, P. J. Lamberson, Tipping points. Quart. J. Polit. Sci. 7, 175–208 (2012).
30 J. Geanakoplos et al., Getting at systemic risk via an agent-based model of the housing market. Am. Econ. Rev. 102, 53–58 (2012).
31 B. Golub, M. O. Jackson, How homophily affects the speed of learning and best-response dynamics. Q. J. Econ. 127, 1287–1338 (2012).
32 S. E. Page, The Model Thinker (Basic, 2018).
33 E. Jen, Robust Design: A Repertoire of Biological, Ecological, and Engineering Case Studies (Santa Fe Institute Studies on the Sciences of Complexit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34 K. Gehl, M. Porter, The Politics Industry: How Political Innovation Can Break Partisan Gridlock and Save Our Democracy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Press, 2020).
35 A. Hirschman, Exit, Voice, and Loyalty: Responses to Decline in Firms, Organizations, and State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集智斑图顶刊论文速递栏目上线以来,持续收录来自Nature、Science等顶刊的最新论文,追踪复杂系统、网络科学、计算社会科学等领域的前沿进展。现在正式推出订阅功能,每周通过微信服务号「集智斑图」推送论文信息。扫描下方二维码即可一键订阅:

点击“阅读原文”,追踪复杂科学顶刊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