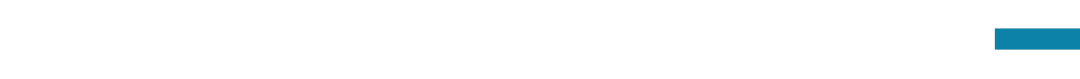1982年,波士顿市开始规划一个隧道项目,该项目将城市的中央主干道I-93重新定向至一条长1.5英里、穿越市中心地下的隧道。这个被通称为“大挖掘”(the Big Dig)的项目,最初预计的总成本为28亿美元,并计划于1998年完成。然而,实际上,工程的施工拖延至2007年,而且最终的费用预计将在2038年前达到220亿美元,包括利息。
在十五年后的1997年,位于加州的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开始建设国家点火设施(National Ignition Facility),该设施的设计目标是创造出一个小型且封闭的空间,以满足核聚变发生的必要条件。最初,预计该项目的成本会达到11亿美元,并在5到7年内完成。然而,实际的建设时间比预期的长了一倍,最终在2009年完成,总成本达到了35亿美元。
在2006年,当夏威夷檀香山高容量交通走廊项目——一条穿越这座天堂之城的20英里轨道交通线——还在规划阶段时,预计的最终成本为40亿美元。然而,近期的估计显示,该项目在2031年完工时的总成本将达到124亿美元[1]。另一方面,位于乔治亚州的阿尔文·W·沃格尔发电厂建设的两座核反应堆项目,其成本比最初预期翻了一番,且比项目获批时预计的时间推迟了5年以上。至于弗吉尔·C·萨默核电站的两个反应堆单元项目,由于无法控制的成本超支,最后不得不被取消[2]。
图1.美国能源部牵头、美国国家科学院撰写的《为美国新型和先进核反应堆奠定基础》报告于2023年发布,讨论了美国如何通过一系列近期政策和实践支持先进核反应堆的成功商业化。该报告的建议解决了缩小技术研究差距、探索新业务用例、改进项目管理和建设、更新法规和安全要求、优先考虑社区参与、加强熟练劳动力以及开发有竞争力的融资选择的需要。
这些例子并非偶然。大规模工程项目——通常被称为“超级项目”,其标价在10亿美元或更高——有其比预期花费更长时间和更多成本的历史。已有大量研究探讨了大型项目有多大可能会出现成本超支和完成时间超出预期的情况。一个被广泛引用的估计是,所有大型项目中有90%的成本超出了最初的预期,而这些大型项目中有大约90%的完成时间也落后于预定计划[3]。其他的观察者给出了不同的估计。尽管如此,即使最乐观的估计也认为至少有50%的大型项目的成本超出了预期。有观察指出,“在超级项目管理的表现上,其表现糟糕得令人震惊,并且在过去70年的可比数据中并未看到改善,至少在成本超支、进度延误和效益短缺这些方面是如此”[3]。除非有重大的改变,我们可以预期成本超支和施工延误将继续困扰大部分的大型工程项目。
在大型超级项目中投资,赌注巨大。全球每年在大型项目上的投入约为6至9万亿美元,这个数字相当全球各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大约8%,而且这个比例每年都在增加[3]。对美国来说,这个挑战尤为突出,因为最近刚刚通过了一项1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改善法案。除非我们能够找到实用的措施,确保大型项目能够按时、按预算完成,并带来预期的效益,否则可能会浪费大量资金,一些重要的大规模项目甚至可能永远无法完成。因此,对于大型项目及其对工程领域的影响,我们急需明确两个基本问题的答案:是什么导致了它们的成本超支和延误,以及未来我们可以如何避免或最小化这些问题?在这个视角中,我们将分别探讨这些“问题”和“可能性”。
为了研究为何大型项目难以按时、按预算完成,学界业界已经投入大量精力。虽然每个项目的具体情况各不相同,但导致问题的大致原因已经十分明朗。首先,这些项目的庞大规模本身就带来了各种挑战。例如,一个预算超过10亿美元且涉及多个利益相关者的项目,每个利益相关者都有各自的目标,而且这些目标往往存在冲突,设计尽量让所有人满意的项目,往往会有一些弱点,这些弱点只有在项目进行过程中才会显现出来。此外,人们通常会有压力让项目尽快启动,例如,担心如果过度延长时间而没有任何进展,支持度就会减弱,这可能导致在所有因素都被考虑到和设计最终确定之前就开始推进项目,期望可以之后再解决细节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在设计阶段花费更多时间,可能会发现的问题在项目启动、施工开始,且已经投入大量资金后才会变得明显。但是,由于大型项目需要的投资和承诺,它们往往会形成一种动力,即使出现重大问题也会继续推进。这就是一个10亿美元的预算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变成30亿美元甚至更多的原因。大型项目的复杂性又引入了一整套完全不同的问题。这些项目有许多相互依赖且以难以预测的方式相互作用的组成部分,这种未预见的互动可能导致出现需要重新思考和重新设计项目的新行为,从而导致延迟和成本增加。
简言之,大型项目的规模和复杂性带来的挑战,在质量和数量上都与小型项目所遭遇的截然不同。要成功应对大型项目的问题,就必须深入理解并妥善处理这些挑战。这些挑战可以归纳为三大类别。首先,技术挑战使得设计、建造及维护大型项目比起小型、较不宏大的项目更具困难性。其次,大型项目的规模、成本和复杂性引发了各种组织、政治和社会问题,这些问题可能妨碍项目的开发、建设和运营。最后,许多工程师、设计机构和建筑公司缺乏应对大型项目所需的培训、专业知识或经验。
大型项目的规模,尤其是复杂性,带来了与小型项目中工程师所遇到的挑战在质性上的不同。在这两个因素中,复杂性是最富挑战性的设计问题的根源。从技术角度看,复杂性与单纯的复杂是有区别的。如鲁布·戈尔德堡机械装置(Rube Goldberg),它由众多部件串联而成(杠杆、球沿滑槽滚动等),其中一个部件的动作会触发下一个部件的动作,这种设备虽复杂,但并非是复杂系统。因为其结果每次都一样。相较之下,复杂系统的各部件以一种使系统行为难以预测的方式相互作用。例如,一个部件的故障可能导致整个系统以完全无法预见的方式运作,甚至发生灾难性失败,就如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因为O型环冻结而爆炸。
由于这种复杂性,大型项目不可避免地具有不可预测性,这可能会产生各种后果。例如,当设计中出现先前未预见的问题时,可能会导致成本超出预算和项目延误。复杂性是许多大型项目遵循所谓的“破-修”模式的主要原因:项目在开始时充满乐观,但对于让其完全运作所需的要求理解不全。然后,在某个时刻,不确定性会赶上来,项目以某种方式“破裂”,需要进行“修补”,即重新设计或重组。由于已经投入了时间、金钱和政治资本,一次“破裂”很少导致整个项目被取消,但会使项目的完成时间延长,成本超出预期。
不成功的大型项目的一个特征是,项目在设计尚未完成就被允许启动。然后随着问题的出现,延误变成了常态,从而带来项目管理的风险。更甚的是,完成项目规划以实现可靠的成本和进度估算的重要性常常被忽视。一个恰当的项目计划应明确为支持开发和验证活动所需的各项行动。它应包含一份风险管理计划,详细列出减少因无法执行的设计、零部件或人员短缺,或者工程开发和验证工作不完备导致的失败可能性和(或)后果的活动。
这些技术挑战并非无法克服,在理想世界中,它们可以被有效应对。然而,大型项目建设所处的现实环境往往远非理想。这些技术挑战还受到项目的组织、政治、社会和专业环境等其他问题的放大。
工程设计过程外的因素会以多种方式影响项目。政治因素和公众舆论会影响项目的需求,并施加成本、时间表和地点的限制。组织因素可能影响设计和施工组织如何协同合作以实现项目。心理因素,如不愿放弃已投入成本的心态,可能会影响对是否继续进行困境中的项目的决定。当然,这些因素会影响任何技术,但在大型项目中,由于大型项目固有的更大不确定性,非技术因素对结果的影响往往更大[4]。
一个很好的例子是所谓的“崇高”所施加的影响。大型项目对工业化社会的人们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它们的规模和力量唤起人们的敬畏和惊奇,同时也让人们为人类能设计和建造如此令人赞叹的事物而感到自豪。这种敬畏和欣赏的情感被称为技术崇高[5,6](technological sublime),类似于被大自然的壮丽,如尼亚加拉瀑布的力量和美丽,或者大峡谷的宏伟所激发的感觉。当然,不同的是,尽管无法创造出尼亚加拉瀑布,但只要付出足够的努力和资源,人类确实有能力建造出三峡大坝。
研究已经表明,技术崇高能够影响对大型项目的决策,包括是否进行以及项目的具体细节[7]。创造一个庞大、强大、美丽或令人印象深刻的物体,并将其献给世界,这种无比吸引人的魅力有助于解释为何一些大型项目会得以建设,即便从经济角度对其成本和收益进行明眼的分析,可能会得出它们并非特别好的投资。
除技术崇高之外,学者本特·弗利维伯格还指出另外三种崇高,它们也鼓励了大型项目的实施。政治崇高指的是政治家们从参与大型项目中得到的满足感;他们可以沐浴在项目的荣光中,并利用它获得政治优势。经济崇高则是企业、工会、工人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从大型项目中流动的巨额资金带来的经济满足。审美崇高则是与大型、美丽的项目如悉尼歌剧院相关的愉悦感;建筑师、设计师乃至与项目无关的人都能欣赏到一个项目如何提升其周围环境,成为人类想象力的地标或纪念物。
这四种崇高共同为大型项目提供强大的推动力,有助于推动临界决策向前发展。由于在大型项目启动前,甚至在项目进行到一半或更多时,通常对成本、时间表和收益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往往没有明确的、客观最佳的决策。因此,主观性起着一定的作用,而这些崇高的元素可以抵消对继续前进的智慧的疑虑或保留意见。
紧密相关的一个问题是工程师和建设公司在估计建设成本和时间时,往往会表现出过于乐观和自信的倾向。当客户要求在特定时间、特定成本下完成项目时,工程师往往相信他们能做到。而建设公司有充足的理由对他们的估计持乐观态度,因为更为悲观(有些人可能会说更为现实)的估计会降低项目得以建设的可能性。在按成本加成方式工作时,建设公司不会因为不切实际的估计而受罚。接受不切实际的预期,会阻碍制定更为现实、可执行的计划,如同深思熟虑的系统工程努力所能制定的计划。其结果之一便是,为了赢得投标,承包商常常会削减性能余量,假设最佳性能,并去掉在特定情况下可能被视为多余但实际上必需的部分。其他类型的倡导者,如希望建设项目的政治家,也倾向于设定不切实际的期望以推销项目。他们会低估成本,设定不切实际的进度,淡化或忽视风险以推动项目的进行。
这些各种因素的综合结果是,带有过于乐观预算和进度的存疑项目得以批准,只是在开发的某处环节“破裂”。然而,如前所述,即使大型项目出现重大问题,也很少导致其被取消。继续推进的动力十分强大,部分原因是已经投入了大量的金钱和时间,部分原因是各种崇高理念依然在发挥作用,部分原因仅仅是因为没人愿意承认犯了错误。实际上,项目常常会继续前行,但在某个点——通常是取消已非可行选项时——问题浮出水面,成本激增。成本超支和延误——有时甚至相当严重——是自然而然的结果。
有些工程师主张,对大型项目持乐观和热情的倾向其实是好事,因为这会带来大量的就业机会和有价值的创新,从苏伊士运河到悉尼歌剧院,我们最终都很高兴能建造出这些项目,但如果事先了解到真实的成本,这些项目可能永远不会实现。1967年,学者阿尔伯特·赫希曼提出了“隐藏之手”的概念。他认为,如果从一开始就明白挑战的真正规模[8],承担被低估困难的技术项目最终会激发人类的创新力,结果是这种创新力使得克服原本不会被接受的困难变为可能。赫希曼列举了几个例子,其中,即使面临无法预见的困难,这种创新力也使得项目能够按时并在预算内完成。然而,遗憾的是,经验显示,这样的情况更多是例外而非常态,被低估的大型项目通常比最初预计的更耗费资金和时间[9]。
然而,过度乐观并非导致大型项目问题的唯一因素。一个主要的因素是,那些负责设计和建造大型项目的人必须处理具有不同优先级和目标的不同利益相关者群体。利益相关者来自各种文化和商业环境,对性能水平、能力、成本、就业和环境影响的看法也各不相同。反应的倾向是尽可能地讨好每个人,这可能导致过度承诺和无法满足冲突目标的不可避免的失败。这可能会由于早期展示实质性进展的政治压力而加剧,例如分包奖励、大量工人的雇佣和早期建设步骤的完成,这又是项目在没有适当规划和审查的情况下开始的另一个因素。相关的因素是,大型项目的“买家”没有熟练的员工来监督设计和建设。他们依赖于承包商,这些承包商并不一定在财务上有“利益关系”,但承包商确实有乐观偏见的激励。解决这个问题可能需要不同的组织和合同关系。
大多数项目销售的压力,使得成本和进度预测过于乐观,这一点甚至超过了工程师的积极倾向。这一点进一步被忽视(或忽略)开发风险的需求所加剧。例如,在航天飞机计划中,这种心态明显,部分可重复使用的发射器是在最初的全面可重复使用的概念被认为无法承受之后的妥协。与阿波罗计划相比,工程师的态度和开发方法与航天飞机开发过程中持续的“推销”有着鲜明的对比。对于阿波罗计划,不需要销售;这是一个国家的承诺。工程师和项目经理愿意公开承认,这是我们深感担忧的新领域,而在航天飞机上并非如此。为了推销该航天飞机计划,人们认为有必要争辩:航天飞机的开发就是逻辑上的下一步,对此科学共同体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更糟糕的是,决定将航天飞机作为美国进入太空的唯一方式。这个决定极大地增加了风险后果,但没有尝试降低灾难性损失的概率。一个适当构建的开发和验证计划(也称为“DVP,development and verification plan”)将允许重新考虑重大设计决策。例如,禁止无人试飞的航天飞机设计是否明智?但由于航天飞机设计只能使用逐段验证来评估,对于一个全新的概念来说,这是一种冒险的方法。
另一个加剧问题的因素是监管流程,其复杂性愈发增长。大量的相关法规意味着在一个大型项目中可能涉及数百个参与者,每个参与者都必须得到妥善处理。项目进度被拖延,成本上升,从而引发各种其他问题。随着时间推移,目标可能会变化,这就需要决定是根据变化调整项目,还是接受最终项目可能并非完全满意[4]。此外,知识和实践随时间而变化,因此在原始设计阶段看似合适的解决方案现在可能已经过时,而新的和改进的方法看起来更值得融入项目中。这又引发了一个抉择,是交付一个需要重新设计和改工的最先进项目,还是坚守原始设计最终得到一个过时的项目[10]。
大多数关于大型项目出现问题的讨论都集中在技术挑战、组织和政治上的不足。然而,工程师和工程组织并不完全无辜。诚然,即使设计完美,也不能保证大型项目的建设能顺利进行,但简单的事实是,大多数工程师和工程机构在处理如今日益普遍的复杂大型项目时并没有做好充分准备。
基本问题在于,很少有人和组织拥有处理大型项目的经验或培训,因此他们往往在工作中学习,尤其是因为大多数项目都是定制的,与已经进行的其他大型项目存在重大差异。此外,这些项目通常采用定制的技术和设计。因此,参与其中的规划者和设计师往往将它们视为非标准的,并假设他们将无法从其他项目的经验中学习[10]。进而,原本可避免的错误就会发生,而从这些错误中可能吸取的教训很少能传递给未来从事类似项目的人员。
一个典型的大型工程项目需要跨越多个领域的经验和能力,包括金融、经济学、社会学、环境政策、政治科学、文化人类学、行为科学和公民参与。然而,负责人往往缺乏领导跨学科项目所需的背景和培训。此外,项目的复杂性使得工程师对将用于项目建设的流程有一定的熟悉度更加重要;没有这种熟悉度,工程师可能会设计出无法以合理价格和及时方式建造的方案。项目越大、越复杂,工程管理人员在不同学科之间移动或与其他专业领域的人进行沟通的能力,以及寻求这种沟通的意愿,就越重要。
同样地,尽管技术娴熟,大多数工程师并不习惯于在设计中思考复杂性和涌现性行为。标准的工程设计假设可以完全指定构建对象的行为——只需考虑一定的小不确定性,并且可以通过检查设计的潜在故障模式,至少从统计学角度来预测故障的发生。然而,由于其复杂性,大型项目打破了这些规则。重大故障更有可能是由于对罕见但并非完全不可能的一系列事件的意外响应。对于一个系统的复杂性及其可能的后果不敏感的工程师很容易开发出一个设计,尤其是在一个大型的、多组件的、多成分的系统中,该设计在大多数情况下都能按计划运行,但当事件以恰好错误的方式对齐时,可能会出现巨大的故障。
在思考如何应对影响大型项目的多个问题时,将解决方案分类与问题分类相平行是有帮助的:技术方法、社会政治组织方法以及提高工程师和工程组织应对大型项目能力的方法。
许多困扰大型项目的技术问题源于项目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使得准确预测性能或预见项目可能出现的故障或无法按预期执行的情况变得困难。因此,不出所料,大多数旨在减少成本超支、时间延误和其他大型项目相关问题的技术方法,都试图找到缓解其复杂性影响的途径。
例如,某些设计决策可以降低项目的复杂性,从而减少涌现行为或导致失败的意外事件序列的可能性。这样的设计之一就是将大型项目分解为尽可能少交互的多个部分。这种策略在多方面都有所助益。它通过降低整个项目的复杂性——特别是减少或最小化需要考虑的交互,从而减轻了工程师的负担,使他们能够专注于各个部分的独立设计。此外,项目的不同部分会有不同的约束和要求。例如,有些部分需要快速变化,而其他部分则有较大的惯性。通过将项目解构为基本可以独立运行的功能子系统,工程师可以让每个子系统在其自身最有效地运行。然而,即使采用这种“模块化方法”,只有在能够准确预见各个模块间的交互作用时,风险才能降低。例如,航天飞机的设计就采用了模块化方式,但在发射过程中出现的意想不到的相互作用导致了失败。因此,有些团队成员需要对整个项目进行全面分析,以确保考虑到任何整体效应。这种方法应有助于促进最有前景的改进机会。
处理复杂性的其他方法包括加入足够的设计余量,以保护项目免受未预见行为的影响,并规避不利事件,这样即便出现了未预见的行为,其后果也不至于灾难性。工程领域的典型做法是设计一个能以期望的方式“行动”的系统。但防止不良行为的设计同样重要,只关注期望行为的结果可能导致设计更易出现非计划的不良行为。
更普遍地说,高效的系统工程能力和技能对于设计和运营达到预期表现的大型项目至关重要。这种更广阔的视角对于开发考虑到项目整体复杂性以及设计各部分如何相互交互的设计是关键。
最后,为大型项目制定适当的性能指标对于确保项目以对用户最有价值的方式运作至关重要。大多数用户并非工程师,他们的价值体系与工程师不同;他们更关心产品完成任务的效果,而非完成任务的方式。相比之下,工程师重视技术性能,因此倾向于关注技术性能而非操作性能指标。换言之,他们可能以技术指标而非用户所看重的事项来衡量系统的成功。因此,他们可能最终建造出一个无法满足期望的系统。为了抵消这种趋势,工程师应该了解用户认为重要的事项,并创建反映这些价值观的操作性能指标。这种明确关注用户需求——以及如何衡量满足这些需求——的重要性仍然显著:一个在技术上无懈可击但无法为用户提供足够价值的大型项目,其失败程度几乎与技术上存在缺陷的大型项目相当。
在大型项目中允许不同团队承担各自的任务,但相互之间的互动交流却很少,这样往往会导致问题在交接处暗藏,直到一切无法挽回才被察觉。对大型项目实施全面的策略,这是一项组织问题。例如,一位高效的项目经理可以确保项目的各个组成部分得到良好的协调,同时负责这些部分的人员能保持紧密的沟通。
此外,紧密连接并协调大型项目的设计与建设阶段是非常重要的。在大多数项目中,设计与建设是分割开的,选定一方进行设计工作,另一方进行施工,两者的选择都基于他们的成本预算。理想情况下,设计与施工的承包商应尽可能紧密地协作。如果他们是两个独立的实体,早期选择建设公司以便在设计初期就与设计师合作是有益的。一种做法是先选定施工承包商,再由该公司选定设计师,这有助于确保两者之间的紧密协作,但在这种情况下,业主对设计的参与度就会降低。另一种方法是首先确定整体设计,然后将大部分详细设计工作交给施工承包商,再由他们与原设计师一起监督剩余的设计工作,确保其符合最初的构想。无论选择哪种方式,目标都是让设计和施工阶段更多地以合作的方式进行,而不是作为独立的任务。
相关的做法是采用集成的工程、采购和合同(EPC,engineering, procurement, and contracting)的合同架构。对于那些拥有成熟技术的小型项目,非协调的方式或许行之有效,因为所有参与者都能被信任独立工作并协同完成。然而,在更大、更复杂的项目中,这种方式可能导致各种意想不到的失败。参与大型项目的组织文化也至关重要。那些最有可能成功的组织,其文化特点是:强调好奇心、谦逊、持续学习、创新和适应性,这些都是管理大型项目中固有不确定性的关键因素。
另一种可能的做法是对已完成的项目设计进行独立的同行评审。这样的评审可能会考虑的因素包括:设计是如何最终确定的;进行了哪些后期设计变更,以及可能产生的改进或错误;设计的实用性(从初始概念到组装);确保充足的安全裕度(并允许进行小幅度的修改,而无需额外的分析和评审);以及环境健康和安全设计的考虑因素[2]。
最后,如何更好地筹备工程师和工程团队以应对大型项目呢?一个关键步骤便是在执行大型项目的各个团队中强调系统工程原理。那些只在自己专业领域内感到自在的人参与复杂项目,往往会酿成灾难。系统工程师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同样重要的还有那些积极寻求并向其他领域的专家学习的人。同样地,工程管理者必须对施工的细节有所了解,以便理解他们的设计对项目总安装成本的影响,这将有助于将大型项目的成本降至最低。鉴于大型项目有时需要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完成,且与项目相关的技术可能会发生变化,因此,能够适应这些变化的灵活设计比不能适应变化的设计更为理想。
或许,改善未来大型项目的最简单且最有效的工程相关步骤之一,就是学习并应用过去的教训。正如前文所述,由于大型项目相对较少且在许多重要方面各不相同,工程师在一个项目中很少有机会应用他们在过去类似项目中学到的经验教训。他们从零开始,几乎没有直接适用于大型项目的培训。这种情况呼唤我们创建一个知识库,例如,包含应采取和应避免的实践清单,解释为何某些方法比其他方法更有效,并提供来自以往大型项目的相关实例。最终,这些经验教训和最佳-最差实践可以作为大学课程、专业研讨会和继续教育的基础。这些教育元素的建立将是对大型项目与其他规模较小的项目在质量上有所不同的认可,它们需要一套独特的技能和能力来设计、建造、维护和运营。未来,大型项目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不能有丝毫马虎。
如今的大型项目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建筑。它们可以包括联合攻击战斗机项目和其他国防项目、大坝、风力发电场、高速铁路系统、机场、重大科学项目(例如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和国家点火设施核工程)、重要的信息和通信技术系统,甚至包括一些大型集装箱船和客轮。每个项目都伴随着风险和不确定性,我们只能管理那些我们愿意承认的风险;那些选择性忽视的风险,终将成为我们的困扰。
多年来的众多评估表明,各类基础设施都接近或已超过其使用寿命,而且对它们的需求已超出最初预期。同时,气候变化的影响,包括海平面上升、极端天气(旱灾和洪灾)以及我们经济需要脱碳的紧迫性,使得在新基础设施上的巨额投资成为了紧要之需。面对如此巨大的挑战,许多对公众福利至关重要的大型项目必须可靠、成功、经济、公平且及时地完成。过去大型项目的诸多失败,要求我们必须采取更为负责任的工程方式。系统工程行业必须挺身而出,迎接这一挑战。
1. Honore M. 2021August 9. For cost overruns, Honolulu Rail is in a league of its own, new data shows. Honolulu Civil Beat. [webpage, accessed 2023 Aug].
2. National Academies of Sciences, Engineering, and Medicine. 2023. Laying the foundation for new and advanced nuclear reactors in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DC): The National Academies Press.
3. Flyvbjerg B. 2014. What you should know about megaprojects and why: an overview. J Proj Manag. 45(2):6–19.
4. Madhavan G. 2022. The grind challenges. Issues Sci Technol. 38(4):17–19.
5. Marx L. 1964. The machine in the garden: technology and the pastoral ideal in America.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6. Nye DE. 1994. American technological sublime. Cambridge (MA): MIT Press.
7. Frick KT. 2008. The cost of the technological sublime: daring ingenuity and the new San Francisco–Oakland Bay Bridge. In: Priemus H, Flyvbjerg B, van Wee B, editors. Decision-making on megaprojects: cost–benefit analysis, planning, and innovation.Northamton (MA): Edward Elgar. p. 239–262.
8. Hirschman AO. 1967. The principle of the hiding hand. The Public Interest. No. 6 (Winter):10–23.
9. Flyvbjerg B, Sunstein CR. 2016. The principle of the malevolent hiding hand; or, the planning fallacy writ large. Social Res. 83(4):979–1004.
10. Söderlund J, Sankaran S, Biesenthal C. 2017. The past and present of megaprojects. J Proj Manag. 48:5–16.
21世纪人类已经进入了全球化时代,事物彼此之间的依赖程度愈来愈深,传统的分割式思维模式已经无法深入分析与解决现有问题。在此时代背景下,一种主张以系统思维模式为核心的科学管理理论顺势而起。
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的复杂性科学,是系统科学发展的新阶段,也是当代科学发展的前沿领域之一。复杂性科学的发展,不仅引发了自然科学界的变革,而且也日益渗透到哲学、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英国著名物理学家霍金称“21世纪将是复杂性的世纪”。
企业、组织都是典型的复杂系统,也是复杂科学可以落地的方向。复杂系统管理学,是建构在复杂系统基础上发展的管理学新视角。复杂系统视角不仅可以形成一个认识问题的体系,也可以孕育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和方法。它不只是一堆解释性的概念,也可以通过与社会科学和大数据相结合,发展算法、构建模型,完成理论验证,发展出可预测未来的动态演化模型。
集智俱乐部邀请了清华大学社科学院社会科学院与公共管理学院合聘教授罗家德,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张勉,SIMOE 和奇弦智能创始人、同济大学组织仿真中心主任陆云波,以及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吕鸿江共同发起了复杂管理学读书季第二季。聚焦在自组织、DAO、创新型管理、网络等方向,分享复杂系统管理领域的前沿理论、经典科普图书,旨在促进学术交流、知识分享以及跨领域合作。共同探讨复杂科学理论在复杂系统管理场景的应用、实践与展望,一起应对复杂多变的人类发展未来。
本系列读书会采用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方式,2023年9月23日开始,每周六下午 14:00-17:00,持续时间预计8-10周。读书会详情及参与方式见后文。

详情请见:
生态型组织进化:混沌边缘的涌现|复杂系统管理学读书会第二季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