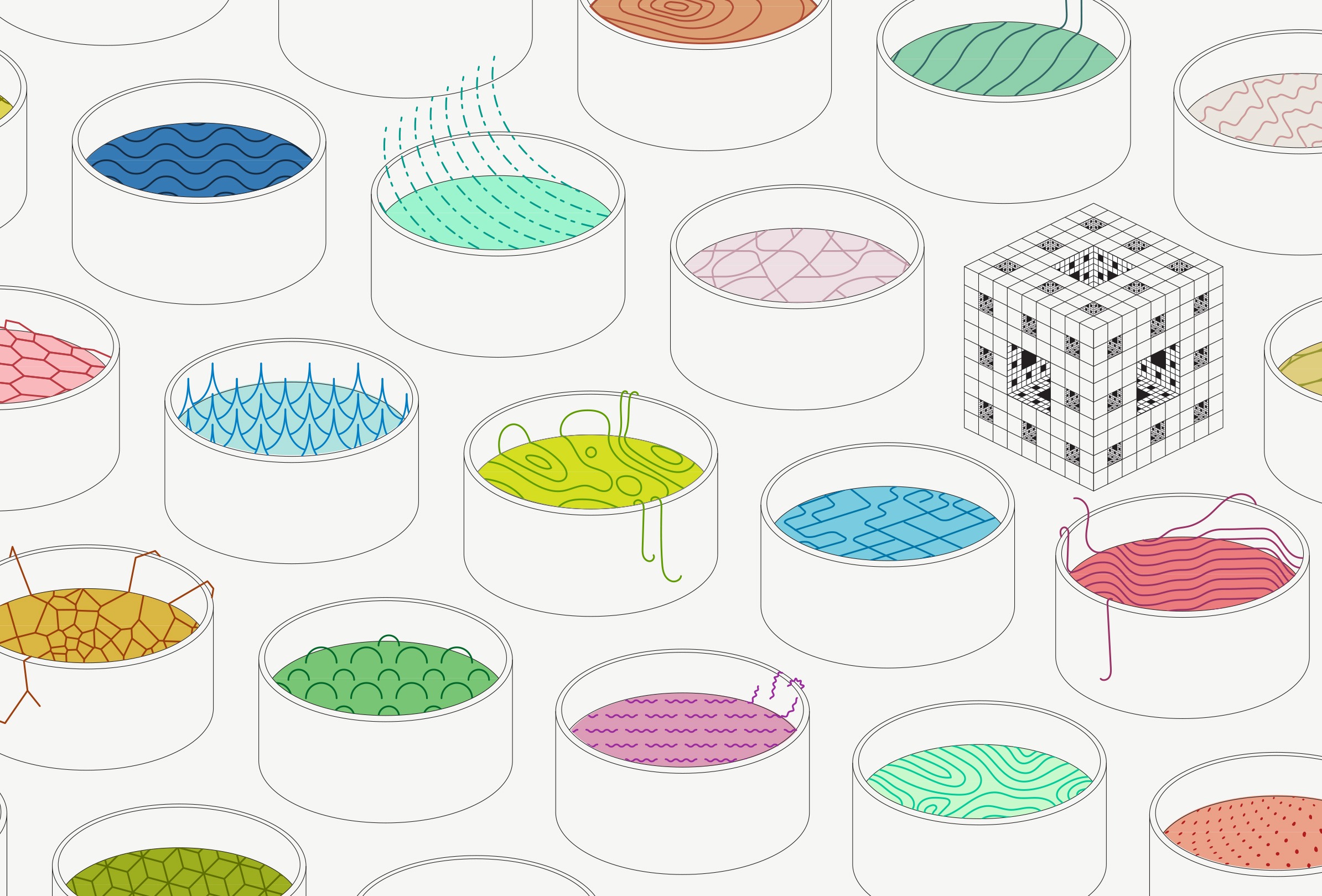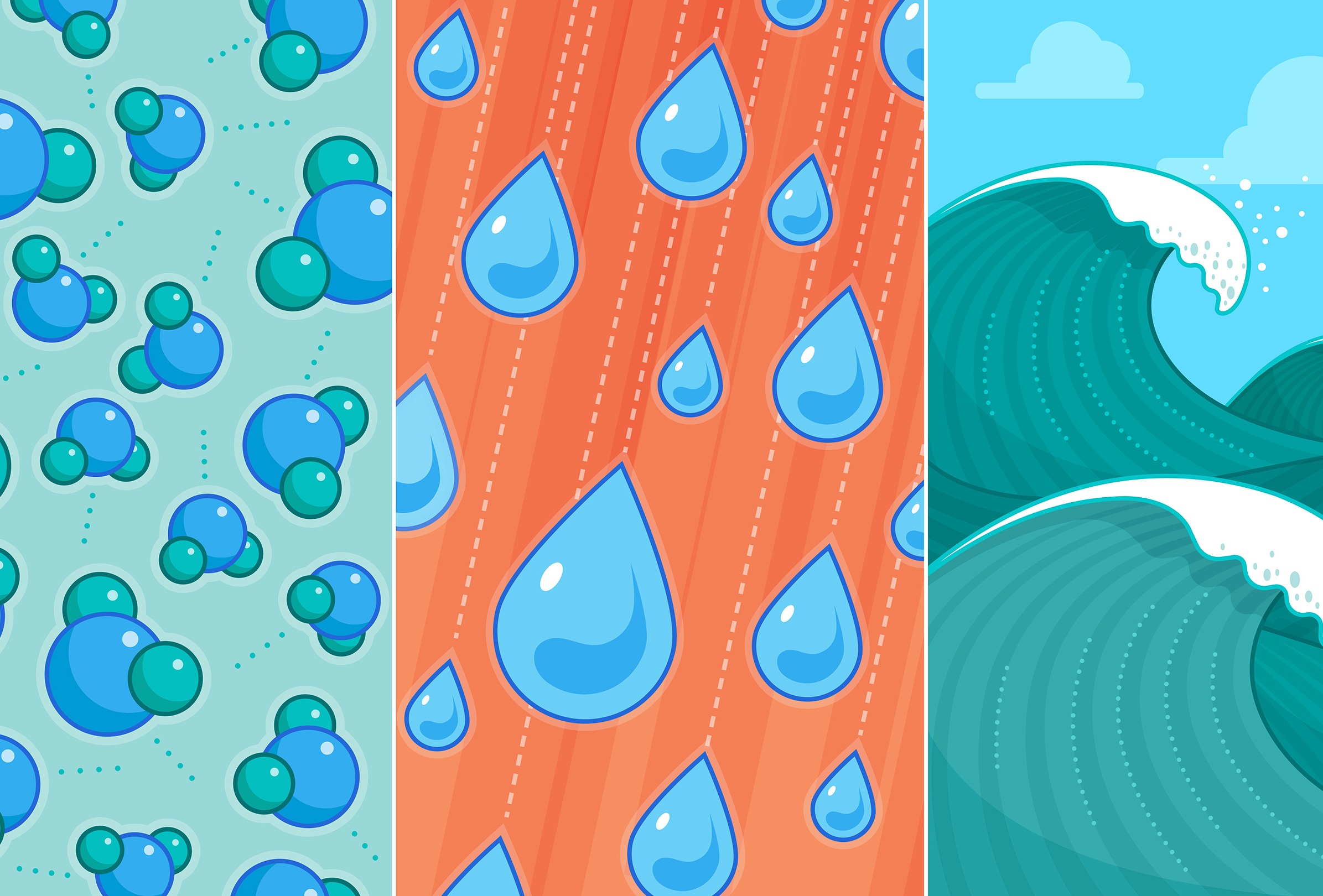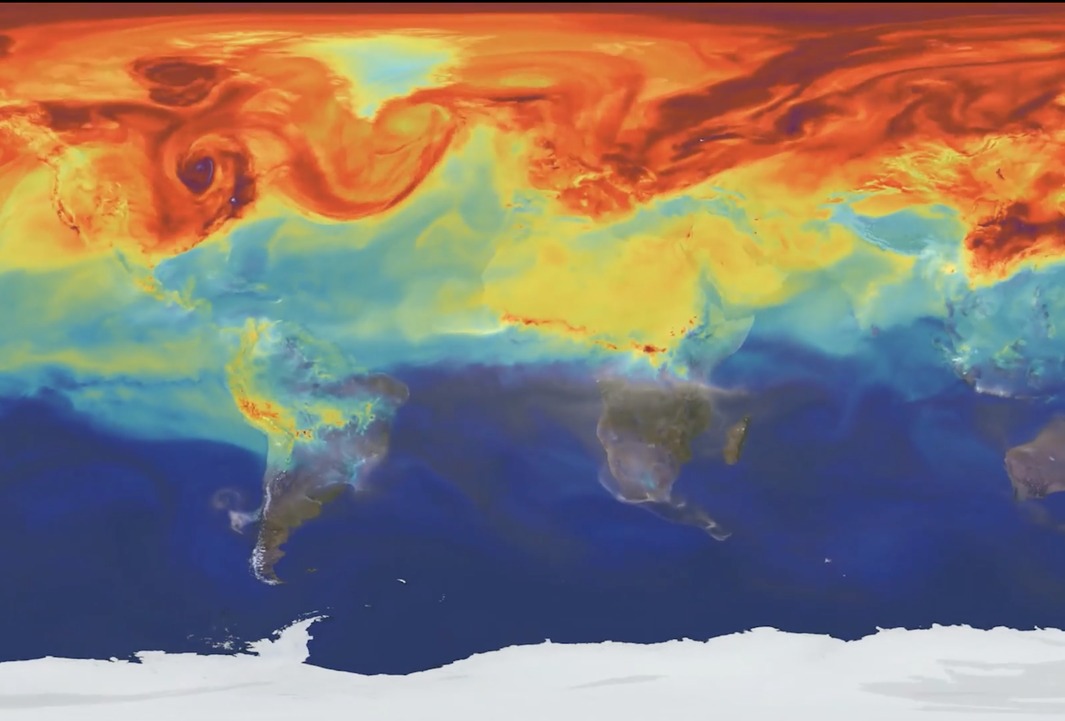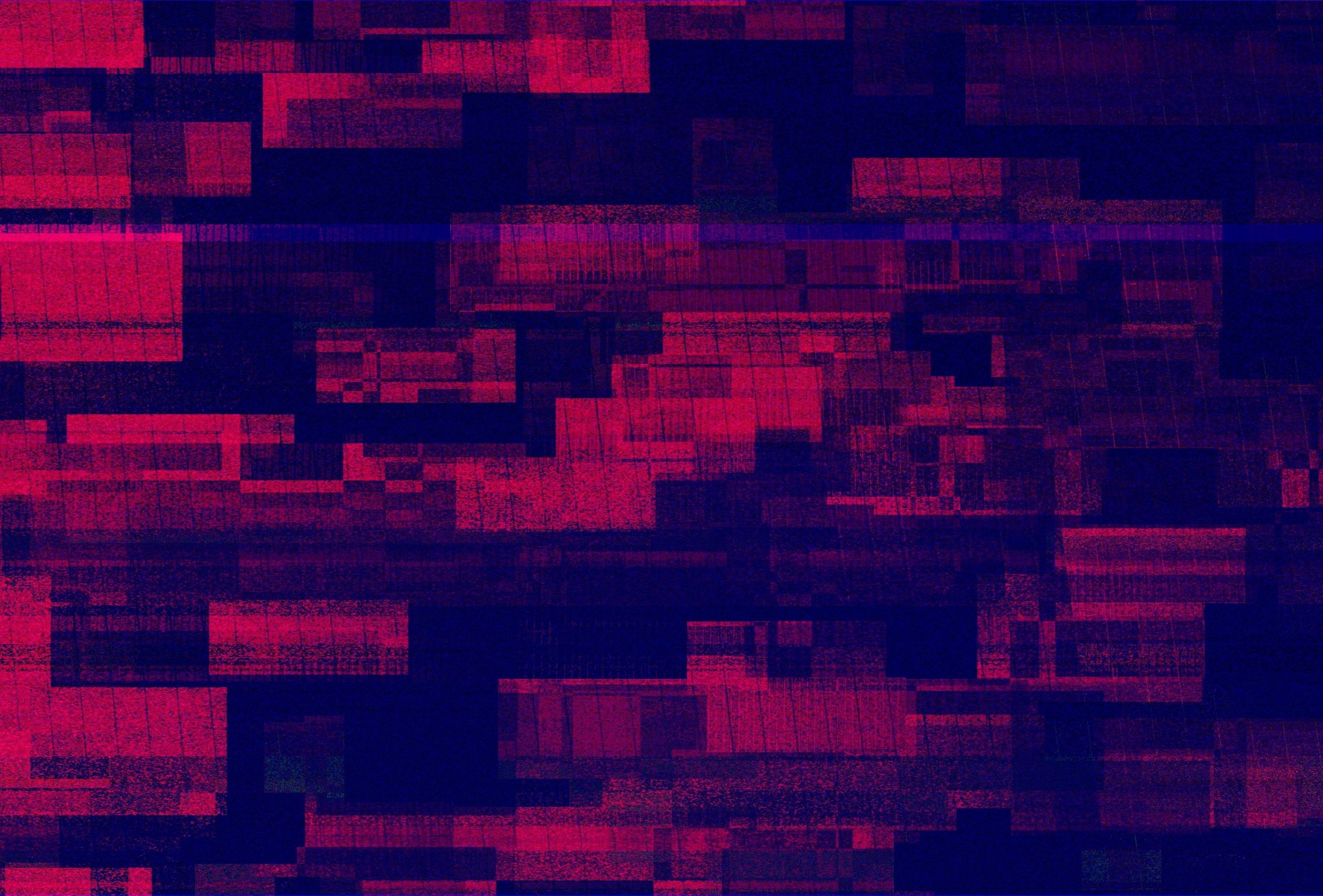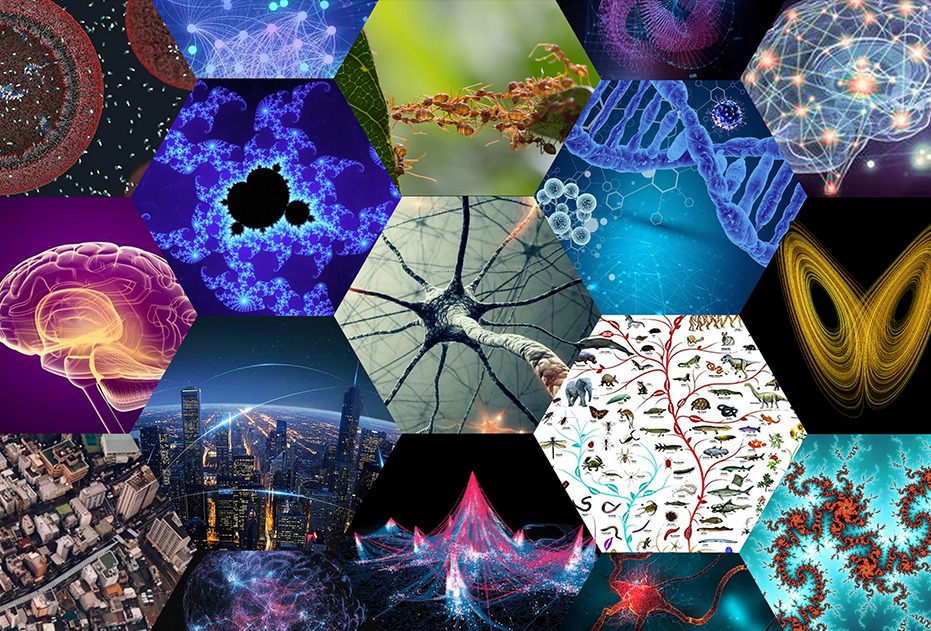Science:人类意识感知的“闸门”——高阶丘脑核团
摘要
已知人类高阶丘脑核团活动与意识状态密切相关,然而这些丘脑核团及丘脑-皮层相互作用如何直接影响人类意识感知的瞬时过程(transient process)尚不明确。我们在植入电极患者执行视觉意识任务时,同步记录了丘脑核团与前额叶皮层(PFC)的立体脑电图数据。与腹侧核团及前额叶皮层相比,板内核与内侧核团(intralaminar and medial nuclei)表现出更早出现且更强的意识相关活动。在意识感知过程中,瞬时的丘脑-前额叶神经同步与跨频段耦合(cross-frequency coupling)均由板内核和内侧核团的θ波相位驱动。由此可见,板内核与内侧丘脑核团在意识感知产生过程中发挥着驱动前额叶皮层活动的”闸门”作用。
关键词:高阶丘脑核团(high-order thalamic nuclei),意识感知,丘脑-前额叶环路(thalamofrontal loop),立体脑电图(sEEG),板内核与内侧核团(intralaminar and medial nuclei),θ波相位同步(theta phase synchronization)
集智编辑部丨作者

论文题目:Human high-order thalamic nuclei gate conscious perception through the thalamofrontal loop
发表时间:2025年4月4日
论文地址:https://www.science.org/doi/10.1126/science.adr3675
期刊名称:Science
探索人类意识背后的神经基础是当代科学中最令人兴奋和最具挑战性的任务之一。传统理论认为,大脑皮层(cerebral cortex)是意识产生的核心,而丘脑(thalamus)仅作为感觉信息的中继站。近期,Science发表的最新研究,通过颅内立体脑电图(sEEG)数据首次揭示:丘脑的板内核(CM/Pf)和内侧核团(MDm)通过θ波相位同步主导前额叶皮层(PFC)活动,像“闸门”一样控制意识感知的瞬时涌现。这一发现为意识理论提供了颠覆性的神经环路证据。
丘脑在意识中的角色:
从“感知觉中继站”到“意识闸门”
丘脑在意识中的角色:
从“感知觉中继站”到“意识闸门”
长期以来,丘脑被视为感觉信息上传至皮层的必经之路,但其是否直接参与意识内容(conscious content)的形成仍存争议。支持“闸门假说”的学者认为,高阶丘脑核团通过广泛连接皮层和皮层下区域整合信息;反对者则认为,功能磁共振(fMRI)等非侵入技术无法捕捉毫秒级的神经动态。本研究使用了一项视觉意识任务(图 1A),让因疾病植入sEEG电极的参与者通过一定的眼动规则给出是否感知到接近阈值光栅(near-threshold grating,图1B)的反馈,同时记录丘脑多个核团与前额叶的神经活动。根据光栅刺激的对比度和参与者的有无意识的反馈,将所有试次划分为四种情况:高对比度-有意识(HC),近阈值-有意识(NC),近阈值-无意识(NU),低对比度-无意识(LU)。研究者对比了“有意识”和“无意识”试次的神经响应,并且将视觉处理与意识相关的特异性活动相剥离,以获得相对“纯净”的意识加工神经过程。

图 1. 视觉意识任务、心理测量曲线和电极定位。(A)视觉感知任务示意图。(B)心理测量检测曲线( Psychometric detection curves)。(上)一个参与者的感知觉百分比示例。(下)所有参与者的数据。图中的每个黑点表示在相关对比水平上的意识百分比,黑色曲线表示拟合的心理测量函数。意识百分比>25%和<75%被定义为接近阈值(near-threshold)。底部示意图中,整体的图片对比度与个体参与者的感知阈值(50%的意识百分比)一致。N,参与者数量;R2,决定系数。(C)在蒙特利尔神经学研究所(MNI)大脑模板上投影的所有记录电极点的左、右、俯视图。红色点表示丘脑的记录部位,蓝色点表示PFC的记录部位。
丘脑板内核与内侧核团的“快速响应”
丘脑板内核与内侧核团的“快速响应”
研究最关键的发现是时间差。在近阈值-有/无意识(NC,NU)的两种情况中,光栅对比度非常相似,所以这两类试次的刺激后神经活动的差异则更多地反映了意识相关的信息,而不是对光栅的简单视觉反应。因此,两种情况的神经活动发散起始时间(DOT)和发散幅度代表了特定记录部位视觉意识相关活动的潜伏期和振幅。结果显示,光栅出现后200毫秒,板内核(CM/Pf)和内侧核团(MDm)已表现出显著的反映意识的事件相关电位(ERP)和频谱扰动(ERSP),而腹侧核团(VA/VLa/VLp)和前额叶外侧区(LPFC)的活动则有时间延迟。这种差异具有解剖学基础:板内核和内侧核团在丘脑中的位置更靠内侧和尾侧(图2E),且与全脑广泛连接。后续解码分析进一步显示,这些核团的神经活动特异性编码“是否意识到”(decoding accuracy 70%),而非光栅物理特征或眼动指令,证实其直接参与意识内容构建。

图 2. 丘脑核团中意识相关活动的特征。(A)每个参与者(P1至P5)在单个记录点的sEEG活动示例。在每个参与者的图中,左图显示了四种不同条件下sEEG活动的总体平均值。曲线的阴影区域表示扫描电镜。两条黑色虚线分别在0和650 ms时表示光栅开始和注视点的颜色变化。粗黑线表示NC和NU条件之间的显著差异(P < 0.01校正,独立样本t检验)。每个面板的右侧显示了在NC(上)和NU(下)条件下的单次试验中的sEEG振幅。每个图中的颜色条表示sEEG振幅。(B ~ D)丘脑核体现意识相关记录位点的百分比(B)、动态百分比(C)和发散开始时间DOTs (D)。在D中,每条内的黑点表示核团内记录位点的DOTs。** p < 0.01。(E)解剖位置与DOTs的相关性。R,相关系数。(F)丘脑核中意识相关活动的振幅。颜色与B所示相同。0和650 ms时两条黑色虚线分别表示光栅起始和定点的颜色变化。(G)丘脑核团的三维重建图。
θ波相位同步:
丘脑驱动前额叶的“神经交流”机制
θ波相位同步:
丘脑驱动前额叶的“神经交流”机制
研究通过相位锁定值(PLV)和相位传递熵(PTE)分析发现,意识出现时,板内核和内侧核团(imTha)的θ波(2-8 Hz)相位会率先同步(图3),并引导前额叶的γ波段(60-150 Hz)振幅振荡。这种跨频段耦合(cross-frequency coupling)呈现明确的方向性:从丘脑到前额叶的信息流强度显著高于反向从前额叶到丘脑的信息流(P = 5.55×10⁻¹⁷),且最抵达的信息出现在前额叶外侧区(LPFC)。研究者比喻:“就像乐队指挥用θ波节拍统一各声部,丘脑通过相位同步将分散的皮层活动整合为连贯的意识体验。”

图 3. 意识相关的丘脑核团-前额叶相位锁定。(A和B)两个参与者(P1和P4)在传感器水平(n*n)的PLV变化。从左到右,在有意识(上图)和无意识(下图)试验中光栅出现后0,100,200,300,400和500ms的时间点,每个记录点之间的PLV。颜色表示PLV (θ波段)。黑线表示丘脑区域和PFC区域的边界。N为记录位点数。(C)根据丘脑核和PFC亚区分组的PLV结果,显示了所有参与者的总体结果。下图显示了有意识和无意识试验之间PLV的差异。(D)丘脑和PFC之间的平均PLV。(左图)所有参与者的总体结果。(右面板)参与者1至5 (P1至P5)的个人结果。(E) θ波段的个体(上图)和群体(下图)PTE结果。(F)丘脑板间核和内侧核(imTha)与PFC亚区之间的平均PLV。(左图)所有参与者的总体结果。(右图)个人结果。对于参与者5,由于采样有限,其他PFC分区的结果缺失。
理论突破:
从“皮层中心论”到“丘脑-皮层双系统模型”
理论突破:
从“皮层中心论”到“丘脑-皮层双系统模型”
这一发现挑战了主流“全局神经元工作空间”(Global Neuronal Workspace)等皮层中心理论。论文提出修正模型:后皮层“热点区”(Hot Zone)生成意识内容初稿后,丘脑板内核和内侧核团作为“闸门”决定是否将其广播至前额叶等高级区域(图4)。这种分工解释了为何丘脑损伤会导致意识障碍(如植物状态),而皮层损伤多影响特定意识内容。研究还暗示,维持觉醒状态(conscious state)与感知内容(conscious perception)可能共享同一套丘脑调控机制。

图 4. imTha和LPFC中意识相关活动的特征。(A) imTha和LPFC中意识相关记录位点的百分比。(B) imTha和LPFC的延迟(DOTs)。灰条和黑条分别表示imTha和LPFC的平均DOTs。每个条形内的彩色点代表每个区域内记录点的点。每种颜色代表每个参与者的数据。** p < 0.01。(C) imTha和LPFC中意识相关活动的振幅。蓝色和橙色的线分别代表imTha和PFC。两条黑色虚线分别在0和650 ms时表示光栅开始和注视点的颜色变化。黑色实线表示imTha和PFC的振幅显著不同的周期。(D、E) imTha和LPFC中与意识相关的ERP位点的θ波段相位集中指数(phase concentration index)。两条黑色虚线分别在0和650 ms时表示光栅开始和注视点的颜色变化。黑色实线表示有意识和无意识状态下相位集中指标显著不同的周期。右边的热图显示了所有意识相关部位的相位集中指数。(F和G) imTha和LPFC的意识相关ERP位点的θ波段大小。与(D)所示相同,但θ波段大小不同。
研究创新与未来展望
研究创新与未来展望
研究的技术亮点在于克服了传统深部脑刺激(DBS)电极覆盖有限的缺陷,利用194个丘脑记录位点和213个前额叶位点的sEEG数据,首次实现人类丘脑核团的高时空分辨率解析。团队设计的视觉任务通过匹配“有/无意识”试次的眼动反应(saccadic response),有效排除了运动报告对神经信号的污染。未来,这一发现可能为意识障碍患者开发针对丘脑的靶向闭环神经调控疗法。尽管研究取得重大突破,但也指出若干开放问题:板内核如何与后皮层“热点区”互动?θ-γ耦合是否存在于其他感知模态?这些谜题有待结合猕猴模型和计算建模进一步探索。这项工作将意识研究从‘相关关系’推向‘因果关系’,为理解大脑最神秘的意识涌现现象打开了新维度。
整合信息论读书会
为什么我们在清醒时有意识,而在无梦的睡眠中意识水平大大降低?为什么我们的意识由大脑的某些部分产生,而非其他部分?为什么大脑的特定部分与视觉和听觉等意识体验密切相关?这些具体的问题本质上涉及到,理解决定一个系统产生意识体验的条件,以及理解决定一个系统具有何种意识的条件。整合信息论(IIT)试图用几何学一般的公理体系来解释意识是什么,意识如何测量。根据该理论,意识对应于一个系统整合信息的能力。
为了深入探索意识奥秘,系统梳理整合信息论的理论体系,北京师范大学系统科学学院教授、集智俱乐部创始人张江领衔发起「整合信息论」读书会,组织对本话题感兴趣的朋友,深入研读相关文献,激发科研灵感。读书会分为以下几个部分:整合信息论综述,基础理论框架,近似计算方法,在神经科学中的应用,在复杂系统中的拓展应用,Φ与系统临界态,以及机器意识。2024年9月28日开始,每周六上午9:00-11:00进行,持续时间预计 10 周,欢迎感兴趣的朋友报名参与!
6. 探索者计划 | 集智俱乐部2025内容团队招募(全职&兼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