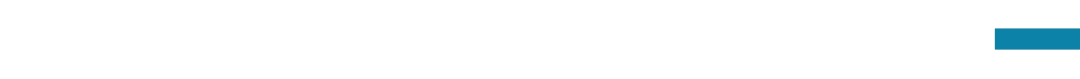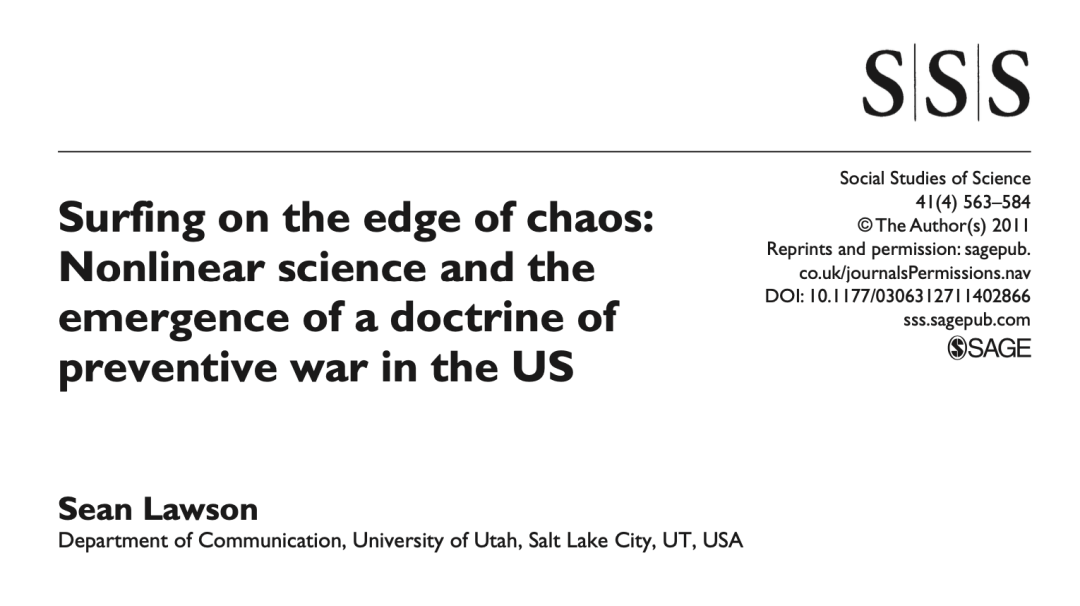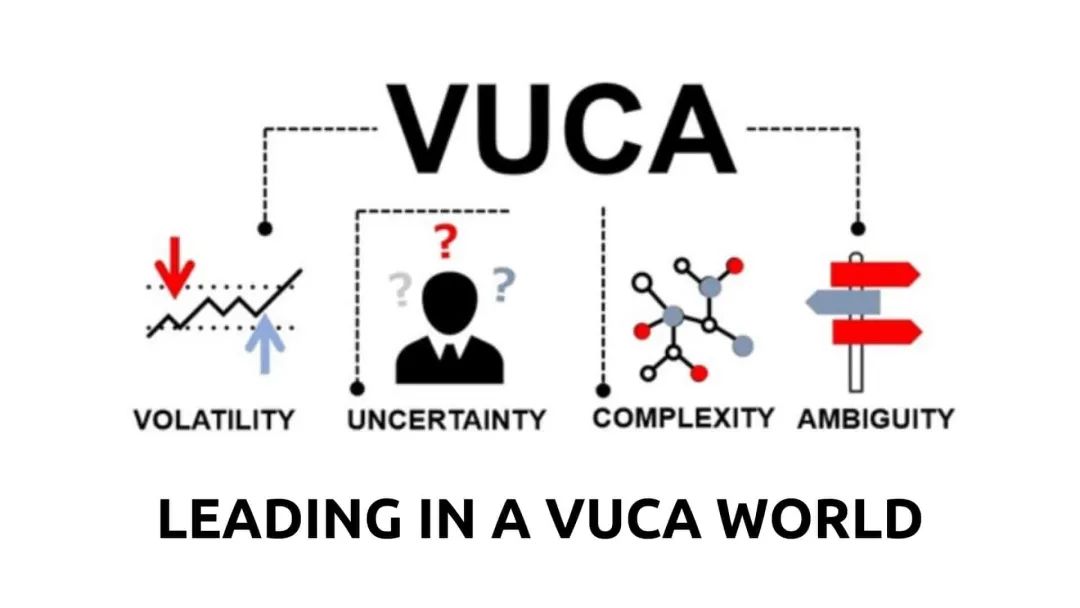非线性理论与复杂性科学已经渗透进社会经济方方面面,包括国际战略与军事斗争。发表于2011年的一篇论文,梳理了作为“新科学”的早期非线性与复杂性研究对美国军事战略思想的影响过程。该⽂认为,在 1990 年代,美国的军事专家和民间国防专家使⽤⾮线性科学的概念和隐喻,将 1980 年代战场战略和战术的原则转化为国际政治和外交政策理论。这些理论认为在更加混乱和危险的后冷战世界中,速度和进攻的必要性。最终,据称从“新科学”中吸取并被证明的“最具军国主义的”教训进⼊了乔治·布什总统领导下的美国国防部最⾼层,并成为迅速采取预防行动、反对“聚集威胁”等策略的基础。除了让我们更好地理解“布什主义”的起源之外,该⽂有助于提升对冷战后美国科学与国家/军队之间关系的理解,特别是科学隐喻在国家安全话语中的作用,这些话语侧重于新信息和通信技术的挑战和机遇。
研究领域:混沌理论,复杂性理论,军事话语,非线性科学
Sean Lawson | 作者
刘培源 | 译者
邓一雪 | 编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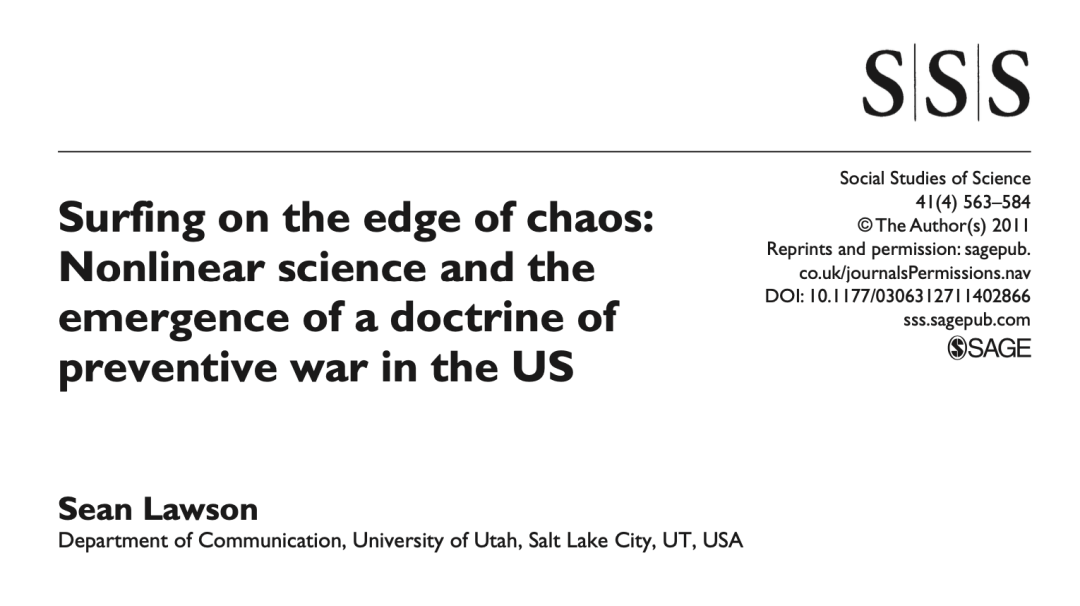
原文题目:
Surfing on the edge of chaos: Nonlinear science and the emergence of a doctrine of preventive war in the US
https://journals.sagepub.com/doi/abs/10.1177/0306312711402866
本文认为,美国国防界从非线性科学中获取概念和隐喻,为乔治·布什政府阐述和使用“预防性战争理论”(doctrine of preventive war)奠定了话语基础。在 1990 年代,美国的军事专家和⺠防专家使⽤⾮线性科学的概念和隐喻,将 1980 年代战场战略和战术的原则转化为国际政治和外交政策理论。这些理论认为在更加混乱和危险的后冷战世界中,速度和进攻的必要性。最终,据称从“新科学”中吸取并被证明的“最具军国主义的”教训进⼊了乔治·布什总统领导下的美国国防部最⾼层,并成为迅速采取预防行动、反对“聚集威胁”等策略的基础。除了让我们更好地理解“布什主义”的起源之外,本⽂还提⾼了我们对冷战后美国科学与国家/军队之间关系的理解,特别是科学隐喻在国家安全话语中的作用,这些话语侧重于新信息和通信技术的挑战和机遇。
关注冷战的科学技术研究(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 STS)学者倾向于强调由美国国家安全情况而建立的新的机构关系和资金模式,可能导致技术科学扭曲。最近的研究试图使这些“扭曲主义”的叙述复杂化,并研究一系列新问题,包括在概念、叙述和想象层面上看待跨越国家/军事技术边界的往来,以及苏联冷战科学家的经历。最后,Hounshell等人表示有必要研究后冷战时期的国家/军事技术关系。
Solovey (2001a: 165) 指出,冷战政治不仅影响了科学知识的产生,而且冷战科学反过来 “促成了那个时代的紧张政治”。不幸的是,大多数研究都集中在国家/军事对技术科学的影响上,而低估了冷战技术科学对冷战主导战略和冷战意义的影响。但也有一些例外,例如 Edwards (1996) 和 Ghamari-Tabrizi (2000, 2005) 关于数字计算机如何启用和塑造冷战话语和战略的研究,以及 Solovey (2001b: 187) 对 20 世纪 60 年代知识论革命中流行病学隐喻的考察。Mellor (2007: 522) 研究了叙事在 20 世纪 90 年代集体“社会想象力”形成中的作用,“在这个过程中,新型武器被想象出来并被解释为必要的”。最后,Gary (1998, 2005) 研究了计算机在美国国防界塑造冷战之后“信息战学说”中的作用。本文通过考察非线性科学在信息时代美国国防界关于国家安全的官方讨论中所起的隐喻作用,将这种关于国家/军事-技术关系的研究延伸到后冷战时期。
STS 学者们雄辩地论证,隐喻在科学知识的产生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Haraway, 1991; Kay, 2000; Keller, 1995, 2000)。Wyatt (2004: 245) 从其工作以及 Lakoff 和 Johnson (1980) 的基础性工作中指出,“隐喻被用作规范和认知的结构化工具”,不仅用于科学知识的生产,而且用于决策者理解和应对大规模技术变革的努力。本文论证了在冷战后,使用武力的理由源于社会想象,其中非线性科学在使国家安全专业人员把技术改变的承诺和危险概念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信息时代,非线性科学的概念和隐喻是表达对社会、技术和战争的理解的关键话语资源。它们还有助于将应对冷战紧急情况的军事学说最终部署为应对911袭击的美国外交政策宗旨,这些学说原本旨在应对20世纪70-80年代的情况。尽管非线性科学似乎提供了理解“新世界秩序(及失序)”的工具,并提供了最适合它的“新科学”,但非线性隐喻最终允许使用者以熟悉的方式理解和应对“新世界”。
类似于 Nelkin 和 Lindee (1995) 追溯流行文化中“基因”含义的演变和扩散的方式,本文追溯了非线性科学的流行理解,如何塑造了世纪之交美国军事和外交政策的形成。它也借鉴了 Eglash (1992, 1998, 2000) 对非线性科学文化史的研究,包括控制论和混沌理论在美国青年亚文化、后现代主义理论家和美国军队中的应用。正如流行的基因概念是遗传科学文化史的核心,美国军方对非线性科学的征募,对于这些学科的发展也很重要。
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为了应对人们眼中的冷战紧急情况,美国军事专业人员就开始将战场描述为“非线性”和“混沌”,认为战场上的速度和进攻是生存的关键。这些概念修辞发展有助于为 20 世纪 90 年代人们对非线性科学兴趣渐涨并越来越多公开讨论铺平了道路。
20 世纪 70 年代初,美国军队面临的最大挑战是苏联在核能力方面的同等地位及其在欧洲常规军事力量的数量优势(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1980; Tomes, 2007: 59, 70)。作为回应,美国国防界开始发展常规战争的技术和理论,使美军以质量优势“抵消”苏联的数量优势。在“抵消战略”中,美国规划者试图利用计算机优势来发展军事力量,这些军事力量日益依赖电子系统来收集战场情报、指挥和控制军队以及向目标运送精确制导“智能”武器 (Tomes, 2007: 63, 67) 。
这些规划者认为,这些新武器系统将导致战场非线性和混沌加剧,并寻求利用这种混乱条件获得战术和战略优势。1982 年,美国陆军引入了一种新的理论,称为“空中作战”,通过该理论,美军将依靠其支持的武器系统来阻截苏联第二梯队的力量,从而减缓苏联的推进速度,直至美军扭转局面并继续进攻(Romjue, 1984: 32-33)。即使没有明确提到非线性科学,该学说的作者也将战场描述为“非线性的”和“混沌的”,取得胜利的关键是掌握主动权,采取攻击性行动,制造并利用混沌和骚乱,对敌人造成不成比例(超额的)的负面影响(见 Hall, 1986:41-42; Wass de Czege, 1984: 109)。
1989 年,海军陆战队也发表了一份更新的出版物。它包含了许多与陆军相同的主题,包括创造一个非线性和混沌的战场。它呼吁海军陆战队学会“在混沌的环境中健壮成长”,并将混乱“作为对付无法应付的敌人的武器”(United States Marine Corps, 1989: 64)。《海军陆战队手册》(Marine doctrine manual)的主要作者John Schmitt上尉声称,“由于战争是 一种流动现象,如果我们随着时间的推移迅速而持续地改变局势,我们的优势就会随着每一次改变而加强” (Schmitt, 1990: 97) 。在 20 世纪 90 年代,非线性、 混沌、速度和进攻将通过从非线性科学畅销书所收集的概念和隐喻的清晰表达,获得科学合法性的光环。
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以及 1991 年沙漠风暴行动中信息化武器的首次大规模使用,导致了 Judith Stiehm (2002: 6) 所说的“ VUCA 世界观”,在这种世界观中,美国军事专业人士认为国际环境变得越来越不稳定、不确定、复杂和模糊。当美国总统乔治·布什和其他人谈论“新世界秩序”时,美国军事领导人却预见了一个没有秩序的世界。在这种焦虑和不确定的环境中,人们第一次看到对非线性科学广泛而公开的提及,并结合了 1980 年代战场战略和战术的教训。
VUCA世界观即Volatility(易变性)、Uncertainty(不确定性)、Complexity(复杂性)、Ambiguity(模糊性)的字母缩写
在 1990 年代,VUCA世界观主导了军事出版物和各级军官声明。甚至在 1980 年代作为“抵消战略”一部分而开发的新型信息化武器也成为VUCA的另一个挑战。在“沙漠风暴”行动中,“智能炸弹”、巡航导弹和隐形战机的壮观画面让电视观众惊叹,同样也震惊了美国国防部的许多人,包括Andrew Marshall领导的网络评估办公室 (Office of Net Assessment, ONA) 的分析师。1991 年,Marshall和他的一位分析师Andrew Krepinevich进行了一项研究,探讨针对伊拉克的“抵消战略”的武器是否构成了“军事技术革命”——这是苏联军方在上世纪 80 年代表达的观点。Marshall的报告《军事技术革命:初步评估》(The Military- Technical Revolution: A Preliminary Assessment)得出的结论是,苏联人在很大程度上是正确的,并认为美国军队应该在组织上和理论上做更多的工作,以兑现其信息技术武器的承诺 (Krepinevich, 1992)。该报告为20 世纪 90 年代和21世纪初的国防辩论设定了议题,这些辩论涉及信息技术引发“军事革命” (RMA) 的承诺和危险。然而, 到了 1994 年,在美国国防规划者中可以发现一种悲观情绪,包括美国国防部网络评估办公室的 Krepinevich,他把这场革命描绘得好像它有自己的生命一样,并对能否“跟上军事技术革命的步伐”表示担忧 (Krepinevich, 1994) 。
技术和组织变革被认为是有效应对冷战后世界挑战的必要条件。鉴于美国军方领导人设定他们无望阻止迅猛的技术变革浪潮,他们认为唯一可能的应对,是发展一支能够快速反应的部队。实现快速反应的关键是通过采用更多的信息技术武器、战略和数字网络化的组织结构来跟上军事革命的步伐 (Sullivan, 1995: 6-8) ,这成为当时的核心倡议。这些最初的应对主要是防御性的,侧重于发展能够迅速面对快速变化的部队,但到了 1990 年代末,美国部队能够而且应该采取预防性行动来推动变革、改变复杂国际事务体系的初始条件的想法,变得越来越普遍。这个想法的部分灵感来自于非线性科学的概念和隐喻。
主要借鉴了越来越多关于非线性科学的流行著作,如James Gleick的《混沌:一门新科学的形成》(Chaos: The Making of a New Science, 1987) ,偶尔也借鉴了流行文化,如Michael Crichton的畅销小说《侏罗纪公园》(Jurassic Park, 1990) ,1993 年成为轰动一时的电影 (Mazarr, 1994)。民间国防专家和军事专家认为,非线性科学概念和隐喻是描述信息时代、VUCA(易变、不确定、复杂、模糊)世界的唯一手段。非线性科学为根据前十年的理论改革进行国际关系和军事事务提供了经验教训,并将成为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军事转型”努力的核心军事理论和战略,以及 2003 年 3 月入侵伊拉克的计划和理由。
虽然早期从非线性科学中吸取经验的努力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得到协调,但它们并没有被忽视。在1996年11月,国防大学(NDU)和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在华盛顿特区资助了 “复杂性、全球政治和国家安全会议”(Complexity, Global Politics, and National Security Conference)。会议汇集了过去十年来在国际关系和军事事务著作中使用非线性科学隐喻的大多数民间专家和军事专家。1996年的NDU会议提供了一个初步的机会,可以介绍受非线性科学启发和证明的有关预防性战争的新生理论,并为以后所有关于非线性科学和国家安全事务的工作提供试金石。此后几年,众多参会人员将对美国国防政策的形态产生深远影响。
会议发言者讨论了两个广泛关切的领域:对国际事务和战争的理论基础与行为。两组非线性主义者都通过一些普遍特征来定义复杂系统。结构上,许多相互关联和相互作用的因子组成了复杂的系统 (Jervis, 1997: 21; Mann, 1997: 62-63; Maxfield, 1997: 79; Rinaldi, 1997: 115; Rosenau, 1997: 36; Schmitt, 1997: 106) 。这些密集的互联和高度的相互作用导致了许多行为特征。首先,它们的行为是“非线性的”,这意味着它们对初始条件的变化具有“敏感性”,因此系统的变化通常不会导致成比例的结果。这种现象有时被称为“蝴蝶效应”,在这种现象中,微小的变化可能导致不成比例的巨大后果,例如蝴蝶在世界的一个地方扇动翅膀,在另一个地方引发飓风 (Jervis, 1997: 22; Mann, 1997: 62; Rosenau, 1997: 37-38; Schmitt, 1997: 107)。其次,复杂系统通常被认为存在于“远离平衡态”,永远是“亚稳定”的,不断变化,并且处于不稳定状态 (Mann, 1997: 62; Maxfield, 1997: 81; Rinaldi, 1997: 115; Schmitt, 1997)。不稳定状态使这些系统本质上不可预测 (Jervis, 1997: 23; Maxfield, 1997: 80; Schmitt, 1997: 107)。因为“开放系统”与其环境交换能量、物质和信息 (Schmitt, 1997: 103) ,系统与其环境“共同进化”。也就是说,复杂系统的变化导致了环境的变化,而环境的变化又反过来导致了复杂系统的新变化。这种“循环因果关系”或“反馈”也经常被认为是复杂系统的一个普遍特征 (Jervis, 1997: 24-25; Maxfield, 1997: 80; Rinaldi, 1997: 115; Rosenau, 1997: 37) 。最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密集的相互联系和非线性的相互作用,通过一个被称为“自组织”的过程,导致可识别模式的“涌现”。因此,该系统的总体特征可能与其组成主体(agent)的特征大不相同,这意味着这些系统可能“大于各部分之和” (Mann, 1997: 62; Maxfield, 1997: 80; Rinaldi, 1997: 115; Rosenau, 1997: 36; Schmitt, 1997: 106)。
早期的非线性主义者一致认为,包括国家、军事、国际政治和战争在内的国际体系本身就是复杂的体系,它们显示出上述各种特征。就战争而言,非线性科学似乎支持过去十年发展起来的陆军和海军学说的宗旨,包括在日益非线性和混沌的战场上迅速采取进攻行动的需要。1989 年《海军陆战队手册》(Marine doctrine) 的作者Major John Schmitt少校甚至告诉美国国防大学的听众,“复杂性理论就是指挥和控制理论”,因为它们都考虑到“众多分布广泛的、各自行动的主体集合,尽管如此,主体仍然可以表现得像一个单一的、甚至是有目的的实体” (Schmitt, 1997: 99)。复杂性理论的主要教训是“指挥和控制的目标不是实现控制,而是让整个组织处于“失控”的边缘,因为那是系统最具适应性、创造性、灵活性和活力的地方。”(Schmitt, 1997: 108)。简而言之,只要己方能够在混沌中茁壮成长,那么混沌就应该受到追捧。虽然 1989 年版的《海军陆战队手册》没有直接提及非线性科学,但在 1996 年,在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的命令下,明确将非线性科学纳入《海军陆战队手册》,Schmitt少校不仅领导了修订《海军陆战队手册1(作战)》的工作,而且还领导了修订其中“战略”和“指挥和控制”章节的工作,所有这些都包含了对非线性科学对战争意义的讨论,这与Schmitt在 1996 年美国国防大学会议上的发言相呼应。
尽管演讲者在会议上为外交政策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经验教训,但国际关系学者和政策制定者利用非线性科学来证明一些长期持有的假设是正确的。由主体相互作用而没有总体规则的复杂系统概念,非常符合新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宗旨。在冷战期间,新现实主义在美国政治学中占主导地位,认为各个国家在一个基本无政府状态的国际体系中相互作用,在该体系中,和平与战争分别是平衡或失衡的结果 (Waltz, 1959, 1979)。
在谈到在一个复杂的国际体系中执行外交政策的后果时,会议发言者有两种想法: 一组发言者提出谨慎,另一组则表示傲慢。在第一组中,Robert Jervis和James Rosenau都提出了在一个被给予蝴蝶效应、反馈和意外后果的复杂国际体系中,单个国家采取有意义行动的能力的问题。Jervis (1997: 21) 警告说,由于“扰乱一个系统会产生多个变化”,因此“结果可能会让始作俑者惊讶”。Rosenau (1997: 34) 对此表示认同,并担心非线性科学“暗示复杂系统是有模式的并且最终是可以被理解的,这可能会鼓励人们过度希望人类的问题能够被解决,并推行旨在解决这些问题的有效政策”。他告诫人们不要试图找到“简单化的公式”,相反,他认为复杂性理论的真正价值在于它“提醒我们没有万用灵药” (Rosenau, 1997: 40-41) 。
尽管如此,空军中将 Ervin J. Rokke,美国国防大学的主席,在他的会议记录中建议,“复杂性理论认为,如果我们只是寻找潜在的简单性或模式,那它们就存在”。“这些理论为我们提供了洞察力,如果不是预测和解决问题的话” (Rokke, 1997: ii)。两位演讲者愿意满足他们客户的需求。与Schmitt倡导的“在混沌边缘冲浪”(surfing on the edge of chaos)类似,Wayne州立大学物理学家Alvin Saperstein和外交官Steven Mann都声称,政策制定者能够而且应该利用国际体系自然而不可避免的混沌,以便改变体系,从而导致理想和可预见的结果。Saperstein (1997: 44-45) 声称,“政策制定者的作用是掌握体系:能够现在就采取行动,从而在未来导致理想的事件,或避免不理想的事件。因此,他/她必须能够预测当前活动的结果。”那么,非专业人士的工作将是“帮助理性的决策者理解进而掌握”。他掌握系统的第一个要求不是“接受战场或世界系统是固定给定的” (Saperstein, 1997: 57) 。由于战场和世界体系始终是混乱和动态的,政策制定者可以通过在比利益体系更低的层次上影响各种因素,来推动变革进程朝着理想的方向发展;例如,在一个国家体系中,试图影响其公民个人可能是明智的,而“国家主权神圣不可侵犯!” (Saperstein, 1997: 57) 。简而言之,他声称,“复杂性的隐喻” 要求人们始终在思考未来。而且,在这些对未来的考虑中,总是包括改变努力领域(即世界体系)本身的尝试 (Saperstein, 1997: 57-58)。
Steven R. Mann,前美国外交官,现任埃克森·美孚集团国际政府关系小组成员。自1976年开始供职于美国外交部门,2003年曾在伊拉克联军临时权力机构任职,在美国外交界为非线性科学概念鼓吹。
对于 Steven Mann (1997: 68) 来说,非线性科学似乎证实了新现实主义的假设,即“国际环境的本质是基于冲突的”。国际舞台上的世界是一个正确的比喻——舞台上没有法律。Mann此后继续担任布什政府负责南亚和中亚事务的首席副助理国务卿,他提出了几项政策建议。他告诫说,“我们应该清楚我们为稳定和为假定的国际准则服务所付出的代价”,包括“多边主义的神话”和“对共同国际价值观的信仰” (Mann, 1997: 67- 68)。他建议,由于“我们现在认为世界处于临界状态”,政策制定者也应该“认识到,并非所有的混乱都是坏事,也并非所有的稳定都是好事”。最后,他建议说,“如果临界状态符合我们的国家利益,例如通过摧毁伊拉克军队和萨达姆政权,我们需要对加速和利用临界状态的方式持开放态度” (Mann, 1997: 67-68)。Saperstein和Mann的外交政策建议呼应了Schmitt等人对战场上部队行为的建议:既然混沌不可避免,美国不仅应该寻求对其作出回应,而且还应该利用和鼓励混沌来造福于自身。只要美国更有能力在混沌的边缘“冲浪”,它就会比任何潜在的对手都有优势。
在 2001 年 9 月 11 日恐怖主义袭击之后,这种观点成为拉姆斯菲尔德国防部高级官员的主流观点,他们为使用预防性战争作为”改变国际体系的初始条件”和防止危险的蝴蝶效应扩散的手段进行辩护,据说这种“系统扰动”来自世界上“不一体化”和“不相连接”的地区。
虽然在美国国务院工作的Mann对布什政府的政策有一定影响力,但同样出席 1996 年国防大学会议的海军中将Arthur K. Cebrowski,在将会议上关于非线性科学、战争和外交政策的想法转化为布什政府官方政策方面发挥了更大的作用。2001 年 10 月,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任命Cebrowski为国防部长办公室(OSD)下新成立的军力转型办公室(Office of Force Transformation, OFT)主任。在总统竞选期间,乔治·布什曾发誓要将冷战时期笨重、缓慢的美国军队转变为一支轻型、灵活、信息时代的军队。军力转型办公室将是概念发展和规划的所在地,以使总统的承诺成为现实,同时也是国防部长的重要咨询机构。在 Cebrowski 领导下,美国军队的“转型”意味着采用“网络中心战” (network- centric warfare, NCW)。
Arthur K. Cebrowski,1942-2005,美国海军中将,曾任美国海军战争学院负责人,2001-2005年担任美国国防部军力转型办公室主任,是网络中心战的主要提出者,在美国军队转型中注入大量复杂系统理念,影响至今。
在被任命为军力转型办公室主任之前,美国国防界已瞥见 Cebrowski 的想法。1997 年 3 月 20 日,他以海军作战部长空间、信息战、指挥和控制主任的身份,在众议院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21 世纪战场的信息优势”的听证会上作证。他的证词是最早公开发表的关于网络中心战的言论之一,首先表达了他对信息技术带来的“信息优势”前景的乐观态度,接受了 Alvin Toffler 和 Heidi Toffler (1993) 的论点,即信息技术的出现开启了一个新时代,即“信息时代” (众议院国家安全委员会, 1997) 。Cebrowski 使用非线性科学的概念和隐喻来描述信息优势的价值,解释说它允许“一个精心构思和精确安排的早期努力产生非常高的变化率,锁定敌人的选择和锁定我们的成功”。他将这些“精确的早期努力”描述为“改变关键的初始条件,排除敌人的选择,并在事情发生之前阻止它”的一种方式。这将允许美国军队发展“强大的自我实现的胜利预期,挫败敌人的士气,同时增加联盟和国内的支持”。这些“自我实现预言”类似于软件行业 “急剧增长的回报率”。他再次回应Toffler夫妇(译注:Alvin Toffler与Heidi Toffler为夫妻,均为美国未来学家)的话说,“这是美国的商业方式,也将是美国的战争方式”(众议院国家安全委员会,1997年) 。
虽然其证词提供了网络中心战的早期一瞥,但Cebrowski 和合著者,空军上尉和斯坦福大学毕业的工程师 John Garstka,更正式地阐述他们的理论,并发表在 1998 年的一篇题为“网络中心战:其起源和未来”的文章中 (Cebrowski & Garstka, 1998)。两人探讨了像沃尔玛这样在地理上分散的大公司是如何通过采用新的信息技术来改变他们的商业策略和运营的。如果国家像制造财富一样制造战争,如果像Toffler夫妇声称的那样,技术推动财富的创造,那么只有通过商业世界来预测战争的未来才有意义。同样,如果一个人也对非线性科学对战争的影响感兴趣,那么看看商业、经济和非线性科学的交叉点是最有意义的。因此,当大多数早期的非线性主义者通过生物学、物理学或化学的类比来寻求经验教训时,Cebrowski 和 Garstka 首先着眼于经济学和商业。
他们转向了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家、圣菲研究所联合创始人W·布赖恩·阿瑟的著作,他是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最早将经济描述为复杂系统的人之一 (Arthur, 1988) 。在旧的工业经济被报酬递减规律所支配的情况下,阿瑟断言,新的信息时代经济将受到“报酬递增”规律的影响,并将之定义为:领先的趋势进一步领先,失去优势的趋势进一步失去优势。增加回报不会产生均衡,而是不稳定:如果一种产品、一家公司或一种技术……凭借偶然或聪明的策略获得成功,增加的回报可以放大这种优势,产品、公司或技术可以继续锁定市场。(Arthur, 1996: 100) 而Cebrowski 和 Garstka (1998)认为,在复杂的非线性战场上取得成功的行为和结构要求与在新经济中取得成功的要求是一样的。网络中心战将“类似于新的经济模式,潜在地增加投资回报……”,锁定“敌人的替代性战略”并锁定“成功”。
军事变革试图通过反映军队内部的复杂性来应对世界这个复杂系统。Cebrowski 和 Garstka (1998) 断言,复杂性理论告诉我们,像军队这样的组织必须自下而上地“自我同步”,这是由于联网的信息技术将提供“信息优势”和“共享意识”。一支知识渊博、网络化和地理分散的部队将允许创造和操纵一个作为复杂系统运作的“非连续”或“非线性”的“战场”。这样一支部队将有能力“改变”复杂的非线性战场空间的“初始条件”,“锁定”敌人的战略 (Cebrowski, 2003a; Cebrowski & Barnett, 2003; Cebrowski & Garstka, 1998) 。
在 20 世纪的最后几年,网络中心战的愿景范围仅限于战场,旨在为美国军队提供必要的灵活性和适应性,以应对 VUCA 世界的危险。即使到了 2000 年,Cebrowski 自己的语言仍然清楚地反映了 VUCA 的世界观:“我们所知道的宇宙是一个综合集成系统,由许多动态相互作用的部分构成。这种系统的未来行为难以或不可能预测”(Cebrowski,2000)。他列出一个判断:VUCA 世界意味着“我们必须为各种各样的威胁做好准备”,而美军将不得不依靠“我们适应形势的能力” (Cebrowski,2000)。他对“宇宙”的描述不仅反映了他对复杂系统本质的理解,还反映了他对美军如何增强适应性的建议。Cebrowski (2000) 援引麻省理工学院管理学教授 Eric Beinhocker 的话说,当面对一个不断变化和不可预测的环境时,“军队应该保持一系列的选择,尽量减少长期和不可逆转的承诺,而不是为了一个单一可预测的未来去优化某个战略”(Beinhocker,1999:97)。
2001 年 9 月 11 日的袭击似乎结束了模棱两可带来的不确定性。这场悲剧意味着“转型”不再是对信息时代抽象挑战的一般性回应。相反,相对于美国 911 事件后的整体“大战略”而言,转型需要被证明是合理的。因此,Cebrowski 和美国国务院军力转型办公室提倡的转型不仅反映了美国在“全球反恐战争”中的战略,而且帮助塑造了美国的战略。
为了将战场之外的变革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Cebrowski 求助于他的朋友 Thomas P.M. Barnett。在 Cebrowski 担任海军战争学院院长期间,作为该学院的一名教员,Barnett 督导了一些研究项目,这些项目旨在“关于民族国家和国民经济相互作用问题上,探索全球化和新经济的兴起如何产生新规则集合”,以及“这些变化如何重新定义美国军方作为美国与世界商业网络关系的‘安全促进者’的历史角色”。当 Cebrowski 成为军力转型办公室主任时,他邀请 Barnett 担任他的战略未来助理。在这个位置上,Barnett致力于“将这种新的解释与我们认为在 9.11 事件中真正具体化的安全环境的转变联系起来……将 9.11 事件实际上视为一个引爆点,具有历史意义”,并且“将转变定位在某种更大的视野中……一个集中的、有序的原则(适用于)国防的使用方式”(Barnett, 2003a)。
Thomas P. M. Baarnett 美国地缘战略学家,发展了地缘政治理论,将世界划分为“功能核心”与“未融合缝隙”,认为美国应该向边缘地带“输出安全”,将其整合进全球化体系中,在美国政策界影响广泛。
在接下来的 3 年里,两人在美国国家安全界宣传他们在 911 事件后提出的“世界运作理论和相应的军事战略” (Barnett, 2003b) ,上至国防部长和副部长级别。他们的理论和战略受到了广泛的欢迎,2001 年到 2002 年间,对简报的需求不断增长。在 2002 年的冬天和 2003 年的春天,人们对Barnett的兴趣真的爆发了,因为Barnett登上《时尚先生》杂志的年度“最佳和最聪明”专刊 (Chaikivsky, 2002)。在 2003 年 3 月的《时尚先生》杂志上,就在美国入侵伊拉克的 18 天前,Barnett的文章《五角大楼的新地图》(The Pentagon’s New Map) 总结了他向五角大楼介绍的想法,以便向读者解释‘为什么我们要打仗,为什么我们要继续打仗’ (Barnett, 2003b; 2004: 267)。2004 年,他将《时尚先生》 的文章整理成一本畅销书。《五角大楼的新地图》详细解释了他和 Cebrowski 向五角大楼领导人提出的理论和策略。
Cebrowski 和 Barnett 的理论和策略将Toffler式的信息时代技术决定论和新现实主义与非线性科学的概念相结合,提倡强有力的经济全球化传播 (Barnett & Gaffney, 2002: 10)。Barnett指出,过去 15 年来,美国大多数军事部署都是在“第三世界”地区进行的,他预测,美国军队最有可能在这些地区进行部署正是因为这些地区没有充分融入全球化。他将世界划分为全球化的“功能核心”(functioning core)和 “未融合裂隙”(non-integarting gap),将后者描述为“受困于制造下一代全球恐怖分子的长期冲突” (Barnett, 2003b)。2002 年 3 月,在向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和沃尔·福威茨(Paul Wolfowitz,时任国防部副部长) 的高级助手作简报时,Barnett (2004: 154) 指出了地图上标出的“未融合裂隙”,并说,“你们看到的是这场战争的战线。这是二十一世纪美军的远征战场。”他后来回忆道,“他们的眼睛突然亮了起来……五角大楼有了一张新地图”。反过来,他认为“一套简单的新安全规则出现了:一个国家保证其对美国军事反应的潜力与其全球化连通性成反比”,或者更简单地说,“脱节定义了危险”(Barnett, 2003b)。
Barnett (2003b)认为,全球化的蔓延和向信息时代的转变将”使各国相互确保相互依存地结合在一起”,从而在长期减少不稳定和冲突。然而,在不久的将来,全球化带来的危险仍然存在。第一,全球“规则集”(即国际行为的法律和规范)已经变得“错位”(Barnett, 2004: 22) ,这些错位反映在国际体系结构、体系中权力的性质以及谁有能力行使这种权力的戏剧性变化上。回顾新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层次分析”,Cebrowski (2003b) 认为,“我们发现权力正向更大的系统层面(而不仅仅是国家层面)移动,而暴力则向下移动到个人层面。其结果可以称为治理缺口(governance gap)。造成这种缺口的原因是我们有不匹配的地方。有些事情只是跑在其他事情的前面。简而言之,全球网络化的信息和通信技术使跨国非国家行为者,例如被 Cebrowski 和 Barnett (2003) 称为“超级个体”和被其他人称为”全球游击队” (Robb,2007) 的“基地组织” ,能够在”更大的系统层面”行使权力并产生影响,而这一层面曾经只有国家才有。因此,在国家和全球行为者没有对超级权力集团和超级个人的出现作出传统反应的情况下,存在着“治理缺口”。用 Cebrowski 的话来说,技术已经“跑在”治理之前了。这个新的、复杂的国际体系被认为更容易受到“系统扰动”——即蝴蝶效应——的潜在破坏性影响,因为其密集的相互联系。Cebrowski (2003a)将“系统扰动”定义为“信息时代的现象,是对国际系统的垂直冲击,水平波从中传播。当它发生时,新的规则被创造出来,于是新的现实被创造出来。这就是我们在 911 之后所看到的。作为回应,他和Barnett说,现在是时候迎头赶上了,美国军队再次成为通过全球反恐战争输出规则的工具。
尽管两人都认为 911 是“治理缺口”中出现的各种危险系统扰动的一个完美例子,但Barnett (2003b) 也在不同场合将 911 描述为一份“礼物”,一个对美国国家安全机构的“巨大恩赐”,以及一个与二战后几年非常相似的“历史创造点” (Barnett & Gaffney, 2002: 1)。Barnett 一直批评 VUCA 在 1990 年代的世界观,因为它没有提供一个可以“指导我们使用军事力量”的”战略概念”。
相反,“冷战后的战略环境被混乱和完全的不确定性所定义,因此我们需要保卫所有,抵抗一切” (Barnett,2004: 19-20)。尽管 911 事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个问题,为所有这些“混乱”和“不确定性”提供了“敌人”,但他担心,正在形成的后911世界观“仍然让我们描述需要防止的可怕未来,而不是需要创造的积极未来”。他认为,这个积极的未来将包括美国致力于“确保全球化的最终目标——我们所知的战争的结束” (Barnett, 2004: 2)。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将称为“全球事务战略”(Global Transaction Strategy),并将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新的预防“规则”作为消除战争的手段。
全球事务战略(GTS)的主要目标是“缩小缺口”——即将经济全球化扩展到第三世界—— 以“掌握系统动荡” (Cebrowski, 2003a)。为此,Barnett (2002: 8) 认为,美国必须努力实现并平衡四种主要的“流动”,包括“能源从缺口流向核心”。实现这种能源从缺口流向核心需要另一种流动,即安全从核心流向缺口,特别是中东。
因此,在全球事务战略中,“输出安全”一词成为建立“基地、海军存在、危机反应活动和军事训练”的委婉说法,以及使用预防性战争来消除威胁全球化的流氓政权 (Barnett & Gaffney, 2002: 6)。他们解释了将安全视为出口的基本原理如下:
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公共部门出口产品的全球市场份额只增加了一个,那就是安全。我们在安全方面的公共开支几乎占全球的一半,与其他任何国家不同,我们实际上可以在大量和持续的基础上将安全出口到其他地区。这就是我们与全球经济的基本交易:我们进口消费和出口安全。
与世界分享我们过剩的安全是我们的独特之处。任何先进的工业国家都可以出售武器,但只有美国才能出口稳定性。是的,它确实引起了一些方面的愤怒,但是从更多方面,它引起了真正的感激——以及对我们“大范围存在”(living large)的宽容。(Barnett & Gaffney, 2002: 3)
Cebrowski (2003a) 回应了这种观点,说“随着时间的推移,缩小缺口是一种道德义务”。他说,结果是“安全出口市场蓬勃发展”。他警告那些抵制全球化的人,“如果你们反对全球化,如果你们反对规则,如果你们反对联网,那么你们可能会引起美国国防部的兴趣。”
因此,将网络中心战与全球技术服务联系起来,证明了通过全球事务战略来改造美国军队的合理性。全球事务战略将允许美国履行其道德义务,缩小“缺口”,从而防止系统动荡,提供“一支由拥有超级权力的个人组成的军队,能够对拥有超级权力的个人发动战争”。通过这种方式,美国的战争方式将军队推向更加集中的全球警察角色:我们越来越专注于消除做坏事的坏人’ (Cebrowski & Barnett, 2003)。Cebrowski (2002)用另一种委婉的说法来表示预防性使用武力,他断言,一个转变了的军队将使美国能够“威慑他国前进”,这将不得不“建立在预防的基础上”。反过来,他将威慑前进等同于改变战场空间和国际系统作为复杂系统的初始条件 (Cebrowski, 2002, 2003b)。
到 2002 年,诸如“路径依赖”、“引爆点”、“溢出效应”和“意外后果”等术语似乎没有指向有意义的个人行动的困难。相反,它们激发了一种信心,甚至超过了 1996 年国防大学会议上 Alvin Saperstein 和 Steven Mann 的过度乐观主义。尽管Mann和Saperstein的结论是,世界体系是混沌的,但最终是可控的,但Barnett (2004: 47) 更加自信,他断言,一旦你知道如何追踪全球化的原因和影响,“从五角大楼的角度来看,那些看起来像是“混沌”的东西就显得有序得多。”Barnett没有采取基于混沌概念的反应性政策,而是主张利用全球化规则集的知识来设计“值得创造的未来”,或者用Saperstein的话来说,改变“努力的领域”。
Cebrowski 和 Barnett (2003: 3) 认为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行动是创造这样一个未来的第一步。他们为未来的战场战争指明了方向,伊拉克战争尤其表明了美国未来多年的国家战略 (Swofford, 2004: 4-5)。根据 Cebrowski (2003a) 的估计,驻伊美军采用和使用网络中心战的结果不亚于“我军从工业时代向信息时代的转变”,以及令人震惊、敬畏,并击败了伊拉克敌人。他希望这在未来的冲突重演:‘我们希望我们所有的敌人,不管是现在的还是将来的,都能看着我们说:‘哇。他们是怎么做到的?我们亲眼目睹了这一切,但我们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也无法阻止它。”这就是转变的力量。
同样,Barnett (2003b) 在 2003 年 3 月美国入侵伊拉克之前解释说,“与萨达姆 ·侯赛因政权在巴格达的军事接触不仅是必要和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好的”。他用全球事务战略来为即将到来的战争辩护,认为伊拉克战争只是“缩小差距”多年计划的第一步:
我支持在伊拉克开战的原因是,由此产生的长期军事承诺将最终迫使美国把整个缺口作为战略威胁环境来对付。中东是最好的切入点。唯一能改变这种恶劣环境并为改变打开闸门的就是外部势力介入并全天候扮演利维坦的角色。推翻萨达姆……将迫使美国扮演比过去几十年更充分的角色……。这项工作将变得非常重要,使得我们在战后德国和日本的长期努力回顾起来显得很简单,就像保姆那样。没有安全,自由就不能在中东开花结果,而安全是这个国家最有影响力的公共部门出口产品。(Barnett, 2003b)
在他的书中,他向读者展示了“通往值得创造的未来的十个步骤”的“充满希望的形象”。前三步包括对那些被总统认定为“邪恶轴心”的国家采取果断的军事行动。继伊拉克战争之后,他建议朝鲜独裁者金正日下台,朝鲜重新统一,他认为“如果布什总统再次当选,这将不可避免” (Barnett, 2004: 379)。第三步是“到 2010 年推翻伊朗的毛拉” (Barnett, 2004: 380)。第四步,随着拟议中的美洲自由贸易区(FTAA)的成功实施,将把美国的注意力重新带回西半球。然而,实现美洲自由贸易协定将需要美国承诺“结束贩毒集团和叛乱组织在哥伦比亚这个失败国家几乎共同的统治”。“这将是一个令人惊讶的混乱任务,如果我们决心要成功,我们必须一路拥抱它” (Barnett, 2004: 380) 。令人惊讶的是,他预测/主张到 2050 年,美国可能会增加十几个州,这是由于美国“精挑细选西半球最好经济体”的结果,(Barnett, 2004: 382)。他相信,如果他的步骤得到遵循,那么“战争的结束就在我们的历史把握之中,我将活着见证这一成就。”如果没有真正的牺牲,那么对于这么多人有价值的未来就不会到来。” (Barnett, 2004: 383)。但在Barnett“充满希望的”愿景中,战争的结束始于战争的牺牲,帮助他解释“为什么我们要打仗,为什么我们要继续打仗” (Barnett, 2003b)。
尽管 Cebrowski 和 Barnett 提出的理论和策略令人恐惧(虽然可能滑稽,但就像奇异博士一样),但是这两个理论和策略对美国的外交和国防政策产生了持久的影响。正如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成立了自己的“竞争情报”组织来“清洗”有关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计划的战前情报一样 (Mitchell, 2006) ,军力转型办公室作为“唯一专门致力于转型的机构”“在正常的商业活动过程之外”工作,拉姆斯菲尔德认为这是他的首要任务。在拉姆斯菲尔德亲自挑选的 Cebrowski 领导军力转型办公室,以及 Cebrowski 亲自挑选的 Barnett 协助他的情况下,两人能够在911袭击和2003年3月入侵伊拉克之间塑造“五角大楼看待敌人、脆弱性和未来结构的方式”。
尽管军力转型办公室于 2006 年 10 月关闭(比罗伯特·盖茨(Robert Gates)接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出任国防部长还早 1 个月),尽管美国随着奥巴马当选总统发生了“政权更迭”,但支持者和批评者都承认,Cebrowski 和军力转型办公室对美国军队产生了持久的影响(Barnett, 2006; DiMascio, 2006)。军力转型办公室的关闭,拉姆斯菲尔德的离开,以及反叛乱(counterin surgency, COIN)理论的兴起,都被认为是对网络中心战、变革和布什主义的否定 (Barry & Thomas, 2007; DiMascio, 2006; Gates, 2009, 2010; Sieff, 2007)。然而,美国陆军战争学院 DIME 博客的一位撰稿人最近正确地指出,“网络中心战从未消失” (Groh, 2010)。Cebrowski 和 Barnett 的理论和策略也没有多少特点。他们认为全球威胁环境是信息时代引发的全球叛乱,这与反叛乱理论的基本假设以及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实施和颁布该理论的努力并没有太大的不同。陆军/海军反叛联合理论,以及《2010 四年防务评估报告》(2010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前者由曾担任伊拉克“增兵”架构师和指挥官、现任奥巴马总统在阿富汗“增兵”指挥官的大卫·彼得雷乌斯(David Petraeus)将军撰写,后者则由盖茨国务卿撰写,两者都认为,全球化和技术发展的结合,使得危险的非国家行为者得以崛起(Department of the Army, 2006: vii; Gates, 2010: 9, 31)。因此,盖茨部长关注的是建立适合反叛乱理论的军事力量,这与新保守主义关于军事力量能够确保一个“新美国世纪”的愿景并没有太大的背离。新保守主义者呼吁建立一支“警察部队” (Donnelly et al., 2000: 10-11) ,Barnett 和 Cebrowski 呼吁建立一支所谓的“系统管理部队”,专门负责清理政权更迭后的混乱局面,这支部队专门负责国家建设(Barnett, 2004; States News Service, 2003)。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系统管理部队”的提议在拉姆斯菲尔德国防部没有得到多少支持,但罗伯特·盖茨领导下的奥巴马国防部接受了Barnett的预测,即“大冲突已经结束,小冲突已经开始”,并优先考虑建立这样一支部队,作为其军事改革努力的核心(Barnett, 2004: 302; Gates, 2009, 2010)。事实上,Barnett赞扬了盖茨,他写道:
作为一个多年来一直在争论将五角大楼的战略视角和资源从大冲突“下调”到小冲突(我喜欢称之为“系统管理”)的人,盖茨原来是我希望他成为的开创性人物。盖茨只是在引导我们为今天的全球安全环境找到一个回到未来的解决方案。这绝不是放弃我们作为全球霸主的角色,相反,这是为了整合看似不可驯服的边界而恢复我们熟悉的工具箱。(Barnett, 2009)
在国防界的语境中,参考非线性科学也继续发挥重要作用。例如,《2010四年防务评估报告》将国际体系视为“一个复杂的环境”,并谈到“战争的复杂性日益增加” (Gates, 2010: 9,31) 。彼得雷乌斯将军的一位主要顾问在撰写《打击全球叛乱》(killcullen, 2004, 2007) 一书时引用了复杂性理论。因此,发现彼得雷乌斯编写的反叛乱理论手册建议“系统思维”是成功镇压叛乱的必要条件并不令人惊讶。“这一要素基于系统科学的观点,该观点旨在理解系统要素的相互关联性、复杂性和整体性” (Department of the Army, 2006: 4-3)。
David Kilcullen,澳大利亚战略学家,2005-2006年任美国国务院反恐协调办公室的首席战略家,是时任美国国防部长彼得雷乌斯的顾问,其反叛乱理论密切借鉴了非线性科学概念。
一般来说,对军事上使用科技隐喻的研究仍然是主流思维模式的一个有价值的指标。Bousquet (2009) 指出,从历史上看,西方军事专业人员经常从科学中寻找概念和隐喻,以帮助他们建立“技术科学秩序体系”,从而帮助战争的理论化、准备和实施。如前所述,科学技术研究(STS)在国家/军事-技术科学关系方面的工作已经证明了技术科学与国家安全话语、想象和政策在冷战期间的相互渗透。网络中心战和全球事务战略的故事,突显了这样一个事实:技术科学继续充当隐喻素材的来源,在美国军事和外交政策的形成和合理化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表明,在军事上使用技术科学隐喻应继续成为学术研究的一个主题。这样的调查帮助我们继续Edwards的工作(1996:41),以“模糊和扭曲在技术科学和知识的边缘和实践之间常常划定的尖锐、整齐的界限,构成其他人类的努力,如政治、商业,或战争”。非线性科学隐喻成为至关重要的修辞技术,使 911 后的安全话语得以清晰地表达,其中包括预防性使用军事力量的关键原则。同样,它们也是学者们寻求理解甚至阐明这种论述的重要工具。科学技术研究学者处于独特的位置,可以在持续的基础上,批判性地参与国家这部分从科学中吸取教训的安全话语。这里展示的工作正是为了做到这一点,同时也呼吁其他人加入这项工作。
Akera A (2007) Calculating a Natural World: Scientists, Engineers, and Computers During the Rise of U.S. Cold War Research. Cambridge, MA: MIT Press.
Alberts DS and Czerwinski TJ (eds) (1997) Complexity, Global Politics, and National Security.
Washington, DC: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Arthur WB (1988) Self-reinforcing mechanisms in economics. In: Arrow KJ and Anderson P (eds)
The Economy as an Evolving Complex System. New York: Wiley, 9–33.
Arthur WB (1996) Increasing returns and the new world of business.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Barnett TPM (2003a) A future worth creating: Defense transformation and the new security envi- ronment. Presentation to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Washington, DC, 11 February.
Barnett TPM (2003b) The Pentagon’s new map. Esquire 139(3) (March): 174. Available at: www. esquire.com/ESQ0303-MAR_WARPRIMER?click=main_sr (accessed 12 March 2011).
Barnett TPM (2004) The Pentagon’s New Map: War and Peace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ew York: G.P. Putnam’s Sons.
Barnett TPM (2006) NCW infiltration: Complete. Thomas P.M. Barnett: Weblog, 27 August. Available at: http://globlogization.wikistrat.com/globlogization/2006/8/27/ncw-infiltration- complete.html (accessed 12 March 2011).
Barnett TPM (2009) Inside the war against Robert Gates. Esquire, 14 April. Available at: www. esquire.com/the-side/richardson-report/robert-gates-new-defense-budget-041409 (accessed 12 March 2011).
Barnett TPM and Gaffney HH Jr (2002) The global transaction strategy. Transformation Trends
Barry J and Thomas E (2007) Blame for the top brass. Newsweek, 22 January, p. 36.
Bassford C (1998) Doctrinal complexity: Nonlinearity in Marine Corps doctrine. In: Hoffman FG and Horne G (eds) Maneuver Warfare Science. Quantico, VA: U.S. Marine Corps Combat Development Command.
Beaumont RA (1994) War, Chaos, and History. Westport, CT: Praeger.
Beinhocker ED (1999) Robust adaptive strategies. MIT Sloan Management Review 40(3): 95–106.
Beyerchen AD (1992) Clausewitz, nonlinearity and the unpredictability of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7(3): 59–90.
Blaker JR (2007) Transforming Military Force: The Legacy of Arthur Cebrowski and Network Centric Warfare. Westport, CT: Praeger Security International.
Bousquet A (2009) The Scientific Way of Warfare: Order and Chaos on the Battlefields of Modernit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Cebrowski AK (2000) President’s forum. Naval War College Review LII(2).
Cebrowski AK (2002) The state of transformation. Presentation to Center for Naval Analyses, Crystal City, VA, 20 November.
Cebrowski AK (2003a) Speech to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Washington, DC, 13 May.
Cebrowski AK (2003b) Network centric warfare and transformation. Presentation to IDGA Network Centric Warfare conference. Arlington, VA, 22 January.
Cebrowski AK and Barnett TPM (2003) The American way of war. Proceedings of the U.S. Naval Institute 129(1): 42–43.
Cebrowski AK and Garstka JJ (1998) Network-centric warfare: Its origin and future. Proceedings of the U.S. Naval Institute 124(1): 28–35.
Chaikivsky A (2002) The best and the brightest: Society – Thomas Barnett. Esquire 138(6) 1 December: 163.
Coram R (2002) Boyd: The Fighter Pilot Who Changed the Art of War. Boston: Little, Brown. Crichton, Michael (1990) Jurassic Park. New York: Knopf.
Dalton JH, Boorda JM and Mundy CE Jr (1997) Forward … From the Sea. Washington, DC: Department of the Navy.
DeLuca K (1999) Articulation theory: A discursive grounding for rhetorical practice. Philosophy & Rhetoric 32(4): 334–348.
Department of the Army (2006) FM 3-24: Counterinsurgency. Washington, DC: Headquarters, Department of the Army.
DiMascio J (2006) Analyst: Rumsfeld’s departure may signal end to defense transformation.
Defense Daily, 9 November.
Donnelly T, Kagan D and Schmitt G (2000) Rebuilding America’s Defenses: Strategy, Forces and Resources for a New Century. Washington, DC: Project for the New American Century.
Earned CGM (1995) The complexity of war: The application of nonlinear science to military science.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Marine Corps War College, Marine Corps University, Quantico, VA.
Edwards PN (1996) The Closed World: Computers and the Politics of Discourse in Cold War America. Cambridge, MA: MIT Press.
Eglash R (1992) A cybernetics of chaos.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History of Consciousnes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Cruz.
Eglash R (1998) Cybernetics and American youth subculture. Cultural Studies 12(3): 382–409. Eglash R (2000) Chaos, utopia, and apocalypse: Ideological readings of the nonlinear sciences.
Nunc Sumus 1(1). Available at: www.rpi.edu/~eglash/eglash.dir/complex.dir/ch_ut_ap.htm (accessed 12 March 2011).
Fogleman RR and Windall SE (1996) Global Engagement: A Vision for the 21st Century Air Force. Washington, DC: Department of the Air Force.
Forman P (1987) Behind quantum electronics: National security as basis for physical research in the United States, 1940–1960. Historical Studies in the Physical and Biological Sciences 18(1): 149–229.
Gates RM (2009) A balanced strategy. Foreign Affairs 88(1): 28–40.
Gates RM (2010)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Report. Arlington, VA: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Gell-Mann M (1994) The Quark and the Jaguar. New York: WH Freeman & Co.
Gerovitch S (2001) Mathematical machines of the Cold War: Soviet computing, American cyber- netics and ideological disputes in the early 1950s.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31(2): 253–287.
Gertz B and Scarborough R (2004) Inside the ring, book shelf. Washington Times, 2 April, p. A05. Ghamari-Tabrizi S (2000) Simulating the unthinkable: Gaming future war in the 1950s and 1960s.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30(2): 163–223.
Ghamari-Tabrizi S (2005) The Worlds of Herman Kahn: The Intuitive Science of Thermonuclear War.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Gleick J (1987) Chaos: Making a New Science. New York: Viking Penguin.
Gray CH (1998) The crisis of infowar. In: Stocker G and Schopf C (eds) Infowar. New York: Ars Electronica.
Gray CH (2005) Peace, War, and Computers. New York: Routledge.
Groh J (2010) Network Centric Warfare (NCW) never went away. DIME Blog. U.S.Army War College, 5 April. Available at: www.carlisle.army.mil/dime/blog/article.cfm?blog=dime&article=97 (accessed 12 March 2011).
Grossberg L (1986) On postmodernism and articulation: An interview with Stuart Hal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Inquiry 10(2): 45–60.
Hall MWM (1986) A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of airland battle doctrine. Military Review, March, pp. 32–43.
Hammond GT (2001) The Mind of War: John Boyd and American Security. Washington: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
Haraway DJ (1991) Simians, Cyborgs, and Women: The Reinvention of Nature. New York: Routledge.
Holland JH (1996) Hidden Order: How Adaptation Builds Complexity. Cambridge, MA: Addison Wesley Publishing Company.
Hounshell DA (2001) Rethinking the Cold War; Rethink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the Cold War; rethinking the social stud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31(2): 289–298.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Committee (1997) Information superiority: Prepared statement of Vice Admiral A.K. Cebrowski. Procurement Subcommittee and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Subcommittee, U.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20 March.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1980) The Military Balance 1980–1981. London: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Jaffe G (2004) At the Pentagon, quirky powerpoint carries big punch. Wall Street Journal, 11 May, p. 1. Jervis R (1997) Complex systems: The role of interactions. In: Alberts DS and Czerwinski TJ (eds) Complexity, Global Politics, and National Security. Washington, DC: National Defense
Kauffman S (1996) At Home in the Universe: The Search for the Laws of Self-Organization and Complexi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Kay LE (2000) How a genetic code became an information system. In: Hughes TP and Hughes AC (eds) Systems, Experts, and Computers: The Systems Approach in Management and Engineering, World War II and After. Cambridge, MA: MIT Press, 463–492.
Keller EF (1995) Refiguring Life: Metaphors of Twentieth-Century Biolog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Keller EF (2000) The Century of the Gen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Kelley M (2004) Unlikely visionary plots Pentagon future. Associated Press, 19 May.
Kilcullen D (2004) Countering global insurgency (version 2.2). Unpublished manuscript. Available at: http://smallwarsjournal.com/documents/kilcullen.pdf (accessed 11 March 2011).
Kilcullen D (2007) Counterinsurgency in Iraq: Theory and practice, 2007. Presentation to Counterinsurgency Seminar, Marine Corps Base, Quantico, Virginia, 26 September.
Kleinman DL (1995) Politics on the Endless Frontier: Postwar Research Policy in the United States.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Krepinevich AF Jr (1992) The Military-Technical Revolution: A Preliminary Assessment.
Washington, DC: Office of Net Assessment, Department of Defense.
Krepinevich AF Jr (1994) Keeping pace with the Military-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Issue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10 (Summer): 23–29.
Krulak GCC (1996) Operational Maneuver From the Sea. Washington, DC: Department of the Navy, Headquarters United States Marine Corps.
Laclau E and Mouffe C (1985)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London: Verso.
Lakoff G and Johnson M (1980) Metaphors We Live B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Lemann N (2001) Dreaming about war. The New Yorker 77(19) (16 July): 32. Available at: www.
comw.org/qdr/0107lemann.html (24 April 2011).
Leslie SW (1993) The Cold War and American Science: The Military–Industrial–Academic Complex at MIT and Stanford.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Lewin R (1992) Complexity: Life At the Edge of Chaos. Macmillan, New York.
Maddrell DO (2003) Quiet transformation: The role of the Office of Net Assessment.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National War College,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Washington, DC.
Makus A (1990) Stuart Hall’s theory of ideology: A frame for rhetorical criticism. Wester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54(4): 495–514.
Mann SR (1991) Chaos, criticality, and strategic thought.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National War College, Washington, DC.
Mann SR (1992) Chaos theory and strategic thought. Parameters (Autumn): 54–68.
Mann SR (1997) The reaction to chaos. In: Alberts DS and Czerwinski TJ (eds) Complexity, Global Politics, and National Security. Washington, DC: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62–68. Maxfield RR (1997) Complexity and Organization Management. In: Alberts DS and Czerwinski TJ (eds) Complexity, Global Politics, and National Security. Washington, DC: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78–98.
Mazarr MJ (1994) The Revolution in Military Affairs: A Framework for Defense Planning.
Carlisle Barracks, PA: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U.S. Army War College.
Mellor F (2007) Colliding worlds: Asteroid research and the legitimization of war in space.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37(4): 499–531.
Mitchell GR (2006) Team B intelligence coups. Quarterly Journal of Speech 92(2): 144–173. Nelkin D and Lindee MS (1995) The DNA Mystique: The Gene as a Cultural Icon. New York:
Osinga F (2007) Science, Strategy, and War: The Strategic Theory of John Boyd. New York: Routledge.
Pentland PA (1993) Center of gravity analysis and chaos theory.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Air War College, Air University, Maxwell Air Force Base, Alabama.
Pillsbury M (2000) China Debates the Future Security Environment. Washington, DC: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Reimer DJ (1996) Army Vision 2010. Washington, DC: Department of the Army.
Rice DB (1992) Global Reach – Global Power: The Evolving Air Force Contribution to National Security. Arlington, VA: Aerospace Education Foundation.
Rinaldi SM (1995) Beyond the industrial web: Economic synergies and targeting methodologies.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School of Advanced Airpower Studies, Air University, Maxwell Air Force Base, Alabama.
Rinaldi SM (1997) Complexity theory and airpower: A new paradigm for airpower in the 21st century. In: Alberts DS and Czerwinski TJ (eds) Complexity, Global Politics, and National Security. Washington, DC: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112–137.
Robb J (2007) Brave New War: The Next Stage of Terrorism and the End of Globalization. Hoboken, NJ: Wiley.
Rokke EJ (1997) Forward. In: Alberts DS and Czerwinski TJ (eds) Complexity, Global Politics, and National Security. Washington, DC: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ii.
Romjue JL (1984) From Active Defense to Airland Battle: The Development of Army Doctrine, 1973–1982. Fort Monroe, VA: Historical Office, United States Army Training and Doctrine Command.
Rosenau JN (1997) Many damn things simultaneously: Complexity theory and world affairs. In: Alberts DS and Czerwinski TJ (eds) Complexity, Global Politics, and National Security. Washington, DC: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32–43.
Saperstein AM (1984) Chaos – a model for the outbreak of war. Nature 309(5966): 303–305. Saperstein AM (1995) War and chaos. American Scientist 83(6): 548–558.
Saperstein AM (1997) Complexity, chaos, and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Metaphors or tools? In: Alberts DS and Czerwinski TJ (eds) Complexity, Global Politics, and National Security. Washington, DC: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44–61.
Saperstein AM (2007) Chaos in models of arms races and the initiation of war: Crisis stability and instability in an international system. Complexity 12(3): 22–26.
Schmitt JF (1990) Understanding maneuver as the basis for a doctrine. Marine Corps Gazette
Schmitt JF (1995) Chaos, Complexity, and War: What the New Nonlinear Dynamical Sciences May Tell Us About Armed Conflict. Quantico, VA: Marine Corps Combat Development Command. Schmitt JF (1997) Command and (out of) control: The military implications of complexity theory. In: Alberts DS and Czerwinski TJ (eds) Complexity, Global Politics, and National Security.
Washington, DC: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99–112.
Sieff M, (2007) Analysis: Harvey’s fall may help U.S. Army. UPI, 6 March.
Slack JD (2006) Communication as articulation. In: Shepherd GJ, St. John J and Striphas T (eds) Communication As … : Perspectives on Theory. Thousand Oaks, CA: Sage Publications, 223–31. Snyder JL and Jervis R (1993) Coping With Complexity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Boulder:
Solovey M (2001a) Science and the state during the Cold War: Blurred boundaries and a contested legacy.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31(2): 165–170.
Solovey M (2001b) Project Camelot and the 1960s epistemological revolution: Rethinking the politics–patronage–social science nexus.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31(2): 171–206.
States News Service (2003) Pentagon considers creating military force dedicated to stability, reconstruction operations. States News Service, 30 December.
Stiehm J (2002) The U.S. Army War College: Military Education in a Democracy.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Sullivan GR (1995) A vision for the future. Military Review (May/June): 4–14.
Sullivan GR, Coroalles AM (1995) The Army in the Information Age. Carlisle Barracks, PA: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U.S. Army War College.
Sullivan GR and Dubik JM (1993) Land Warfare in the 21st Century. Carlisle Barracks, PA: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U.S. Army War College.
Sullivan GR and Dubik JM (1994) War in the Information Age. Carlisle Barracks, PA: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U.S. Army War College.
Swofford F (2004) Interview with Arthur K. Cebrowski, Director, Office of Force Transformation.
Defense AT&L (March/April): 2–9.
Toffler A and Toffler H (1993) War and Anti-War: Survival At the Dawn of the 21st Century.
Boston: Little Brown & Co.
Tomes RR (2007) U.S. Defense Strategy From Vietnam to Operation Iraqi Freedom: Military Innovation and the New American Way of War, 1973–2003. London: Routledge.
United States Marine Corps (1989) FMFM 1: Warfighting. Quantico, VA: United States Marine Corps.
United States Marine Corps (1997a) MCDP 1-1, Strategy. Quantico, VA: United States Marine Corps.
United States Marine Corps (1997b) MCDP 1, Warfighting. Quantico, VA: United States Marine Corps.
United States Marine Corps (1997c) MCDP 6, Command and Control. Quantico, VA: United States Marine Corps.
Waldrop MM (1992) Complexity: The Emerging Science at the Edge of Order and Chaos.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Waltz KN (1959) Man, the State, and Wa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Waltz KN (1979)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McGraw-Hill.
Wang J (1999) American Science in an Age of Anxiety: Scientists, Anti-Communism, and the Cold War. Chapel Hill, NC: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Wass de Czege H (1984) Army doctrinal reform. In: Clark AA (ed.) The Defense Reform Debate: Issues and Analysi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01–120.
Wyatt S (2004) Danger! Metaphors at work in economics, geophysiology, and the Internet. Science, Technology, & Human Values 29(2): 242–261.
计算社会科学作为一个新兴交叉领域,越来越多地在应对新冠疫情、舆论传播、社会治理、城市发展、组织管理等社会问题和社科议题中发挥作用,大大丰富了我们对社会经济复杂系统的理解。相比于传统社会科学研究,计算社会科学广泛采用了计算范式和复杂系统视角,因而与计算机仿真、大数据、人工智能、统计物理等领域的前沿方法密切结合。为了进一步梳理计算社会科学中的各类模型方法,推动研究创新,集智俱乐部发起了计算社会科学系列读书会。
新一季【计算社会科学读书会】由清华大学罗家德教授领衔,卡内基梅隆大学、密歇根大学、清华大学、匹兹堡大学的多位博士生联合发起,自2022年6月18日开始,持续10-12周。本季读书将聚焦讨论Graph、Embedding、NLP、Modeling、Data collection等方法及其与社会科学问题的结合,并针对性讨论预测性与解释性、新冠疫情研究等课题。读书会详情及参与方式见文末,欢迎从事相关研究或对计算社会科学感兴趣的朋友参与。
详情请见:
数据与计算前沿方法整合:计算社会科学读书会第二季启动